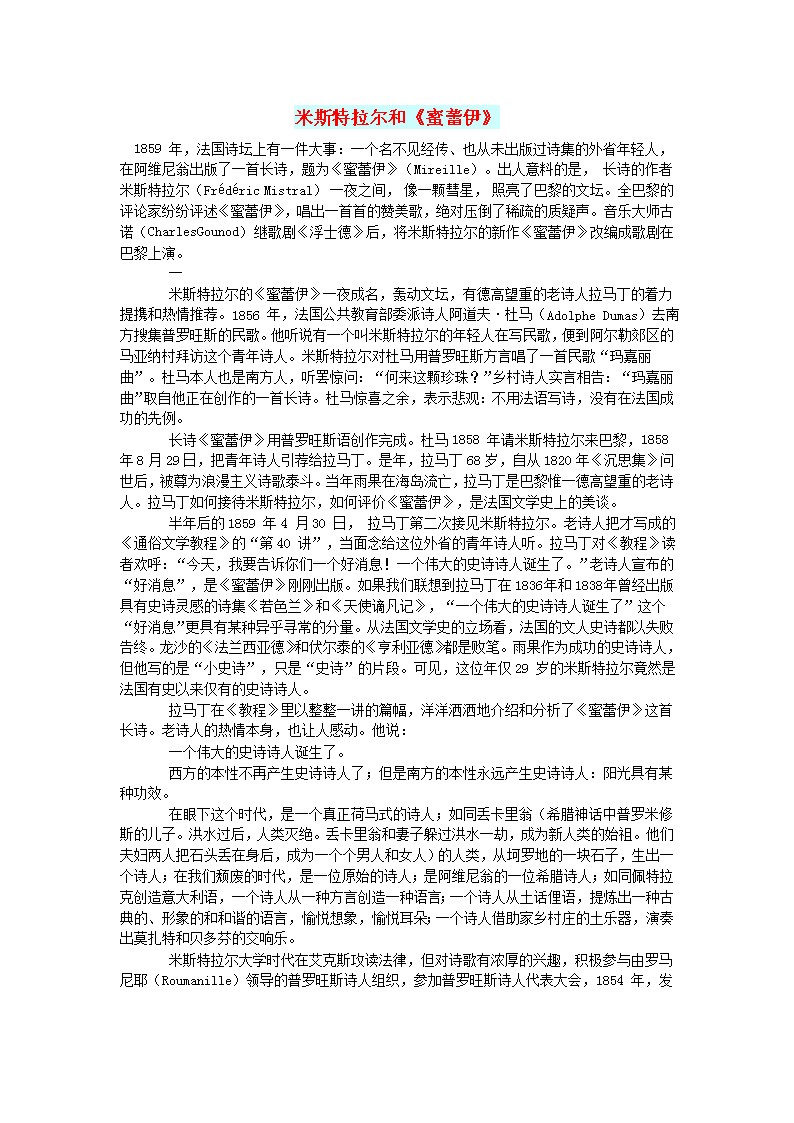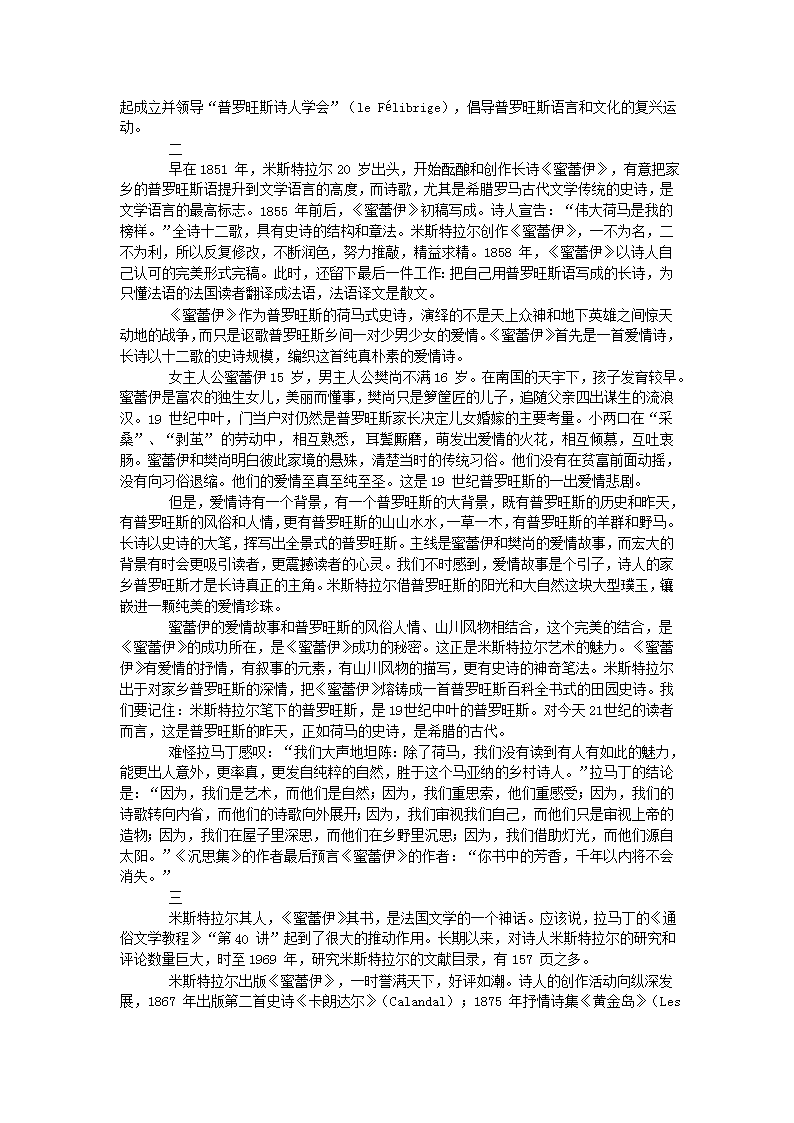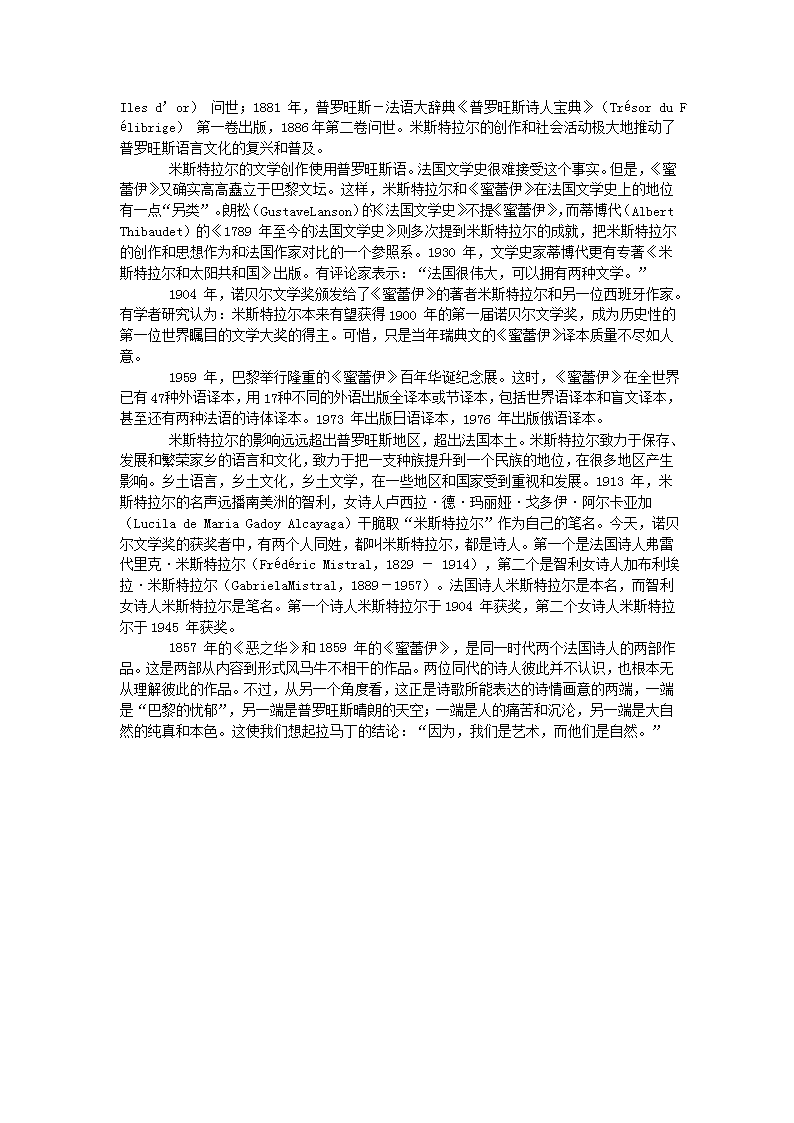- 24.67 KB
- 2022-06-16 12:42:59 发布
- 1、本文档共5页,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可选择认领,认领后既往收益都归您。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先通过免费阅读内容等途径辨别内容交易风险。如存在严重挂羊头卖狗肉之情形,可联系本站下载客服投诉处理。
- 文档侵权举报电话:19940600175。
米斯特拉尔和《蜜蕾伊》 1859年,法国诗坛上有一件大事:一个名不见经传、也从未出版过诗集的外省年轻人,在阿维尼翁出版了一首长诗,题为《蜜蕾伊》(Mireille)。出人意料的是,长诗的作者米斯特拉尔(FrédéricMistral)一夜之间,像一颗彗星,照亮了巴黎的文坛。全巴黎的评论家纷纷评述《蜜蕾伊》,唱出一首首的赞美歌,绝对压倒了稀疏的质疑声。音乐大师古诺(CharlesGounod)继歌剧《浮士德》后,将米斯特拉尔的新作《蜜蕾伊》改编成歌剧在巴黎上演。 一 米斯特拉尔的《蜜蕾伊》一夜成名,轰动文坛,有德高望重的老诗人拉马丁的着力提携和热情推荐。1856年,法国公共教育部委派诗人阿道夫·杜马(AdolpheDumas)去南方搜集普罗旺斯的民歌。他听说有一个叫米斯特拉尔的年轻人在写民歌,便到阿尔勒郊区的马亚纳村拜访这个青年诗人。米斯特拉尔对杜马用普罗旺斯方言唱了一首民歌“玛嘉丽曲”。杜马本人也是南方人,听罢惊问:“何来这颗珍珠?”乡村诗人实言相告:“玛嘉丽曲”取自他正在创作的一首长诗。杜马惊喜之余,表示悲观:不用法语写诗,没有在法国成功的先例。 长诗《蜜蕾伊》用普罗旺斯语创作完成。杜马1858年请米斯特拉尔来巴黎,1858年8月29日,把青年诗人引荐给拉马丁。是年,拉马丁68岁,自从1820年《沉思集》问世后,被尊为浪漫主义诗歌泰斗。当年雨果在海岛流亡,拉马丁是巴黎惟一德高望重的老诗人。拉马丁如何接待米斯特拉尔,如何评价《蜜蕾伊》,是法国文学史上的美谈。 半年后的1859年4月30日,拉马丁第二次接见米斯特拉尔。老诗人把才写成的《通俗文学教程》的“第40讲”,当面念给这位外省的青年诗人听。拉马丁对《教程》读者欢呼:“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一个伟大的史诗诗人诞生了。”老诗人宣布的“好消息”,是《蜜蕾伊》刚刚出版。如果我们联想到拉马丁在1836年和1838年曾经出版具有史诗灵感的诗集《若色兰》和《天使谪凡记》,“一个伟大的史诗诗人诞生了”这个“好消息”更具有某种异乎寻常的分量。从法国文学史的立场看,法国的文人史诗都以失败告终。龙沙的《法兰西亚德》和伏尔泰的《亨利亚德》都是败笔。雨果作为成功的史诗诗人,但他写的是“小史诗”,只是“史诗”的片段。可见,这位年仅29岁的米斯特拉尔竟然是法国有史以来仅有的史诗诗人。 拉马丁在《教程》里以整整一讲的篇幅,洋洋洒洒地介绍和分析了《蜜蕾伊》这首长诗。老诗人的热情本身,也让人感动。他说: 一个伟大的史诗诗人诞生了。 西方的本性不再产生史诗诗人了;但是南方的本性永远产生史诗诗人:阳光具有某种功效。 在眼下这个时代,是一个真正荷马式的诗人;如同丢卡里翁(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洪水过后,人类灭绝。丢卡里翁和妻子躲过洪水一劫,成为新人类的始祖。他们夫妇两人把石头丢在身后,成为一个个男人和女人)的人类,从坷罗地的一块石子,生出一个诗人;在我们颓废的时代,是一位原始的诗人;是阿维尼翁的一位希腊诗人;如同佩特拉克创造意大利语,一个诗人从一种方言创造一种语言;一个诗人从土话俚语,提炼出一种古典的、形象的和和谐的语言,愉悦想象,愉悦耳朵;一个诗人借助家乡村庄的土乐器,演奏出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交响乐。 米斯特拉尔大学时代在艾克斯攻读法律,但对诗歌有浓厚的兴趣,积极参与由罗马尼耶(Roumanille)领导的普罗旺斯诗人组织,参加普罗旺斯诗人代表大会,1854年,发
起成立并领导“普罗旺斯诗人学会”(leFélibrige),倡导普罗旺斯语言和文化的复兴运动。 二 早在1851年,米斯特拉尔20岁出头,开始酝酿和创作长诗《蜜蕾伊》,有意把家乡的普罗旺斯语提升到文学语言的高度,而诗歌,尤其是希腊罗马古代文学传统的史诗,是文学语言的最高标志。1855年前后,《蜜蕾伊》初稿写成。诗人宣告:“伟大荷马是我的榜样。”全诗十二歌,具有史诗的结构和章法。米斯特拉尔创作《蜜蕾伊》,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所以反复修改,不断润色,努力推敲,精益求精。1858年,《蜜蕾伊》以诗人自己认可的完美形式完稿。此时,还留下最后一件工作:把自己用普罗旺斯语写成的长诗,为只懂法语的法国读者翻译成法语,法语译文是散文。 《蜜蕾伊》作为普罗旺斯的荷马式史诗,演绎的不是天上众神和地下英雄之间惊天动地的战争,而只是讴歌普罗旺斯乡间一对少男少女的爱情。《蜜蕾伊》首先是一首爱情诗,长诗以十二歌的史诗规模,编织这首纯真朴素的爱情诗。 女主人公蜜蕾伊15岁,男主人公樊尚不满16岁。在南国的天宇下,孩子发育较早。蜜蕾伊是富农的独生女儿,美丽而懂事,樊尚只是箩筐匠的儿子,追随父亲四出谋生的流浪汉。19世纪中叶,门当户对仍然是普罗旺斯家长决定儿女婚嫁的主要考量。小两口在“采桑”、“剥茧”的劳动中,相互熟悉,耳鬓厮磨,萌发出爱情的火花,相互倾慕,互吐衷肠。蜜蕾伊和樊尚明白彼此家境的悬殊,清楚当时的传统习俗。他们没有在贫富前面动摇,没有向习俗退缩。他们的爱情至真至纯至圣。这是19世纪普罗旺斯的一出爱情悲剧。 但是,爱情诗有一个背景,有一个普罗旺斯的大背景,既有普罗旺斯的历史和昨天,有普罗旺斯的风俗和人情,更有普罗旺斯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有普罗旺斯的羊群和野马。长诗以史诗的大笔,挥写出全景式的普罗旺斯。主线是蜜蕾伊和樊尚的爱情故事,而宏大的背景有时会更吸引读者,更震撼读者的心灵。我们不时感到,爱情故事是个引子,诗人的家乡普罗旺斯才是长诗真正的主角。米斯特拉尔借普罗旺斯的阳光和大自然这块大型璞玉,镶嵌进一颗纯美的爱情珍珠。 蜜蕾伊的爱情故事和普罗旺斯的风俗人情、山川风物相结合,这个完美的结合,是《蜜蕾伊》的成功所在,是《蜜蕾伊》成功的秘密。这正是米斯特拉尔艺术的魅力。《蜜蕾伊》有爱情的抒情,有叙事的元素,有山川风物的描写,更有史诗的神奇笔法。米斯特拉尔出于对家乡普罗旺斯的深情,把《蜜蕾伊》熔铸成一首普罗旺斯百科全书式的田园史诗。我们要记住:米斯特拉尔笔下的普罗旺斯,是19世纪中叶的普罗旺斯。对今天21世纪的读者而言,这是普罗旺斯的昨天,正如荷马的史诗,是希腊的古代。 难怪拉马丁感叹:“我们大声地坦陈:除了荷马,我们没有读到有人有如此的魅力,能更出人意外,更率真,更发自纯粹的自然,胜于这个马亚纳的乡村诗人。”拉马丁的结论是:“因为,我们是艺术,而他们是自然;因为,我们重思索,他们重感受;因为,我们的诗歌转向内省,而他们的诗歌向外展开;因为,我们审视我们自己,而他们只是审视上帝的造物;因为,我们在屋子里深思,而他们在乡野里沉思;因为,我们借助灯光,而他们源自太阳。”《沉思集》的作者最后预言《蜜蕾伊》的作者:“你书中的芳香,千年以内将不会消失。” 三 米斯特拉尔其人,《蜜蕾伊》其书,是法国文学的一个神话。应该说,拉马丁的《通俗文学教程》“第40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长期以来,对诗人米斯特拉尔的研究和评论数量巨大,时至1969年,研究米斯特拉尔的文献目录,有157页之多。 米斯特拉尔出版《蜜蕾伊》,一时誉满天下,好评如潮。诗人的创作活动向纵深发展,1867年出版第二首史诗《卡朗达尔》(Calandal);1875年抒情诗集《黄金岛》(Les
Ilesd’or)问世;1881年,普罗旺斯-法语大辞典《普罗旺斯诗人宝典》(TrésorduFélibrige)第一卷出版,1886年第二卷问世。米斯特拉尔的创作和社会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普罗旺斯语言文化的复兴和普及。 米斯特拉尔的文学创作使用普罗旺斯语。法国文学史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是,《蜜蕾伊》又确实高高矗立于巴黎文坛。这样,米斯特拉尔和《蜜蕾伊》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一点“另类”。朗松(GustaveLanson)的《法国文学史》不提《蜜蕾伊》,而蒂博代(AlbertThibaudet)的《1789年至今的法国文学史》则多次提到米斯特拉尔的成就,把米斯特拉尔的创作和思想作为和法国作家对比的一个参照系。1930年,文学史家蒂博代更有专著《米斯特拉尔和太阳共和国》出版。有评论家表示:“法国很伟大,可以拥有两种文学。” 190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蜜蕾伊》的著者米斯特拉尔和另一位西班牙作家。有学者研究认为:米斯特拉尔本来有望获得1900年的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历史性的第一位世界瞩目的文学大奖的得主。可惜,只是当年瑞典文的《蜜蕾伊》译本质量不尽如人意。 1959年,巴黎举行隆重的《蜜蕾伊》百年华诞纪念展。这时,《蜜蕾伊》在全世界已有47种外语译本,用17种不同的外语出版全译本或节译本,包括世界语译本和盲文译本,甚至还有两种法语的诗体译本。1973年出版日语译本,1976年出版俄语译本。 米斯特拉尔的影响远远超出普罗旺斯地区,超出法国本土。米斯特拉尔致力于保存、发展和繁荣家乡的语言和文化,致力于把一支种族提升到一个民族的地位,在很多地区产生影响。乡土语言,乡土文化,乡土文学,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受到重视和发展。1913年,米斯特拉尔的名声远播南美洲的智利,女诗人卢西拉·德·玛丽娅·戈多伊·阿尔卡亚加(LuciladeMariaGadoyAlcayaga)干脆取“米斯特拉尔”作为自己的笔名。今天,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中,有两个人同姓,都叫米斯特拉尔,都是诗人。第一个是法国诗人弗雷代里克·米斯特拉尔(FrédéricMistral,1829-1914),第二个是智利女诗人加布利埃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Mistral,1889-1957)。法国诗人米斯特拉尔是本名,而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是笔名。第一个诗人米斯特拉尔于1904年获奖,第二个女诗人米斯特拉尔于1945年获奖。 1857年的《恶之华》和1859年的《蜜蕾伊》,是同一时代两个法国诗人的两部作品。这是两部从内容到形式风马牛不相干的作品。两位同代的诗人彼此并不认识,也根本无从理解彼此的作品。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正是诗歌所能表达的诗情画意的两端,一端是“巴黎的忧郁”,另一端是普罗旺斯晴朗的天空;一端是人的痛苦和沉沦,另一端是大自然的纯真和本色。这使我们想起拉马丁的结论:“因为,我们是艺术,而他们是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