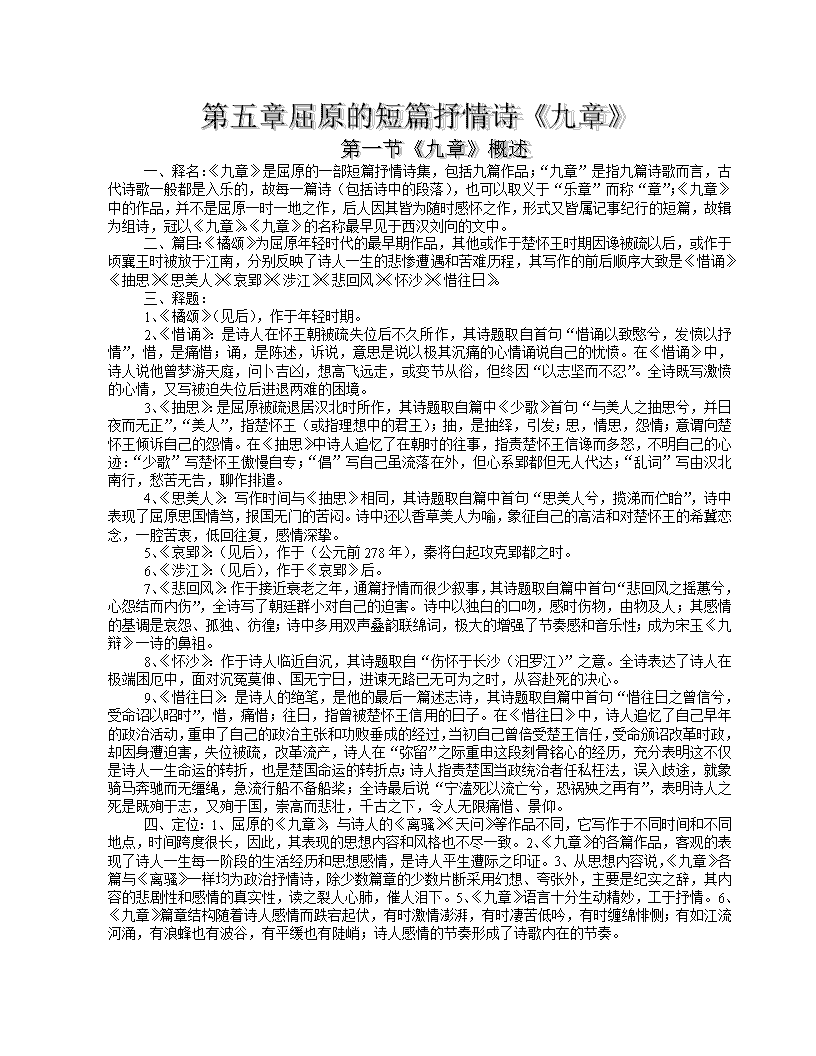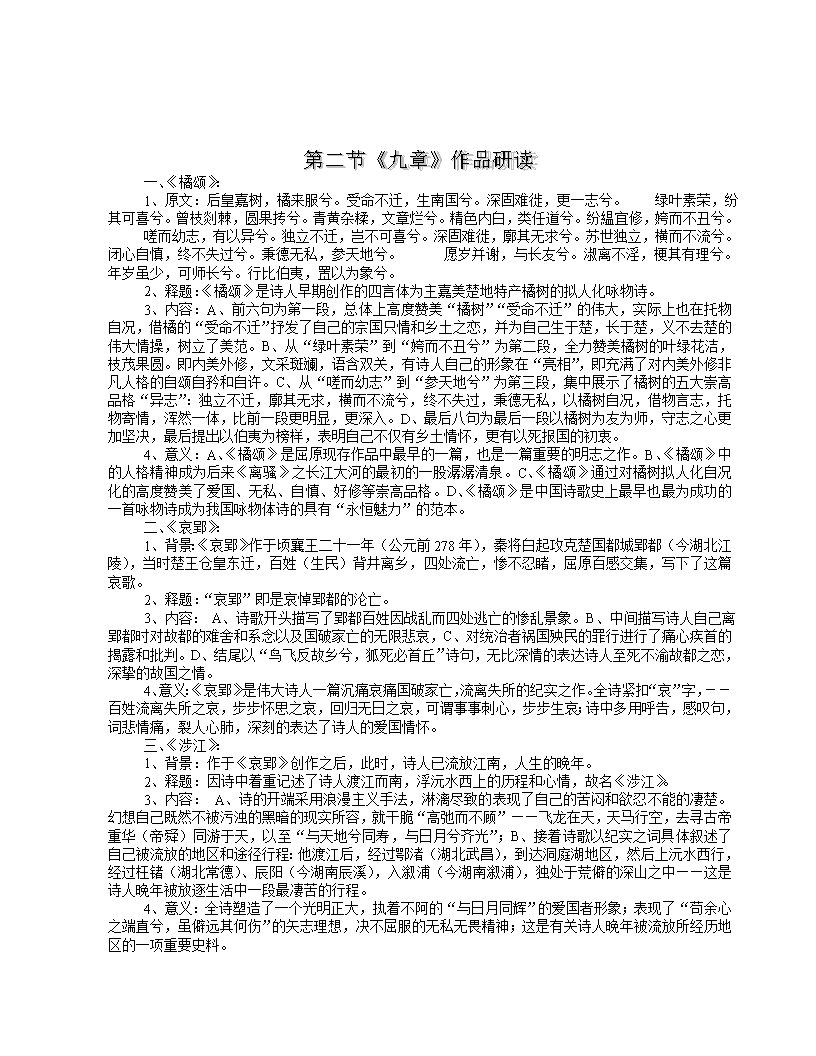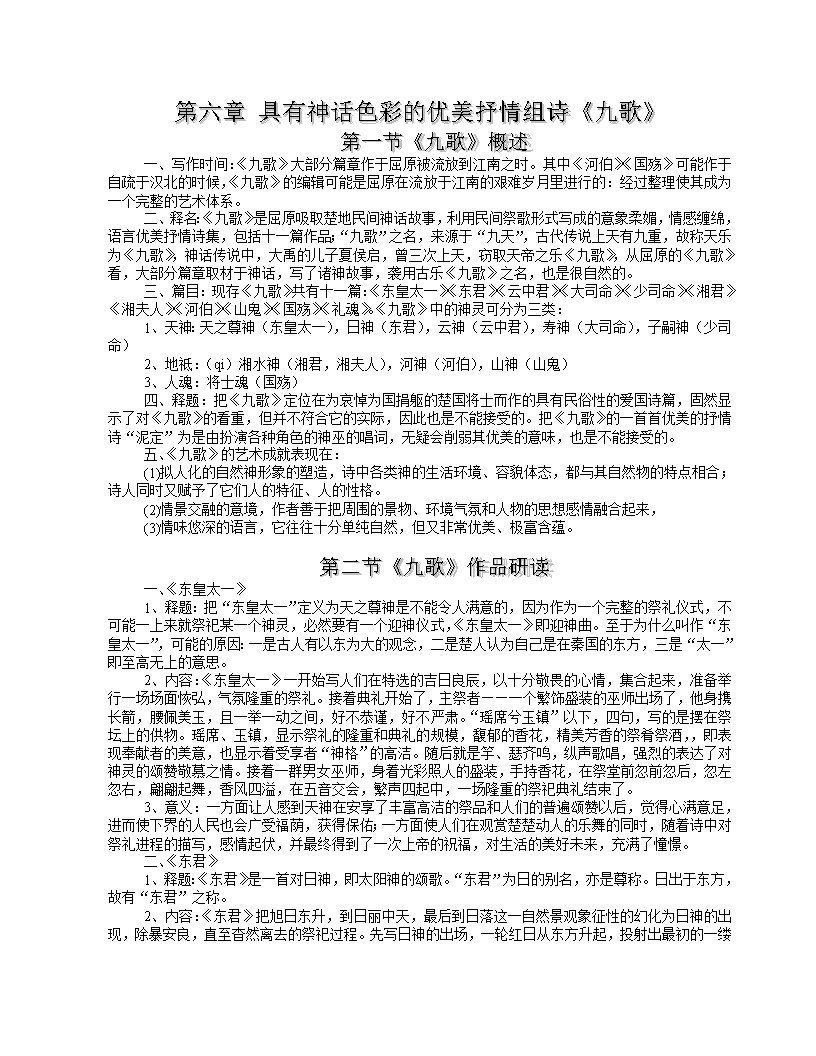- 30.00 KB
- 2022-06-16 12:11:25 发布
- 1、本文档共5页,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可选择认领,认领后既往收益都归您。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先通过免费阅读内容等途径辨别内容交易风险。如存在严重挂羊头卖狗肉之情形,可联系本站下载客服投诉处理。
- 文档侵权举报电话:19940600175。
第五章屈原的短篇抒情诗《九章》第一节《九章》概述一、释名:《九章》是屈原的一部短篇抒情诗集,包括九篇作品;“九章”是指九篇诗歌而言,古代诗歌一般都是入乐的,故每一篇诗(包括诗中的段落),也可以取义于“乐章”而称“章”;《九章》中的作品,并不是屈原一时一地之作,后人因其皆为随时感怀之作,形式又皆属记事纪行的短篇,故辑为组诗,冠以《九章》。《九章》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文中。二、篇目:《橘颂》为屈原年轻时代的最早期作品,其他或作于楚怀王时期因谗被疏以后,或作于顷襄王时被放于江南,分别反映了诗人一生的悲惨遭遇和苦难历程,其写作的前后顺序大致是《惜诵》《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悲回风》《怀沙》《惜往日》。三、释题:1、《橘颂》(见后),作于年轻时期。2、《惜诵》:是诗人在怀王朝被疏失位后不久所作,其诗题取自首句“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惜,是痛惜;诵,是陈述,诉说,意思是说以极其沉痛的心情诵说自己的忧愤。在《惜诵》中,诗人说他曾梦游天庭,问卜吉凶,想高飞远走,或变节从俗,但终因“以志坚而不忍”。全诗既写激愤的心情,又写被迫失位后进退两难的困境。3、《抽思》:是屈原被疏退居汉北时所作,其诗题取自篇中《少歌》首句“与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无正”,“美人”,指楚怀王(或指理想中的君王);抽,是抽绎,引发;思,情思,怨情;意谓向楚怀王倾诉自己的怨情。在《抽思》中诗人追忆了在朝时的往事,指责楚怀王信谗而多怒,不明自己的心迹:“少歌”写楚怀王傲慢自专;“倡”写自己虽流落在外,但心系郢都但无人代达;“乱词”写由汉北南行,愁苦无告,聊作排遣。4、《思美人》:写作时间与《抽思》相同,其诗题取自篇中首句“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诗中表现了屈原思国情笃,报国无门的苦闷。诗中还以香草美人为喻,象征自己的高洁和对楚怀王的希冀恋念,一腔苦衷,低回往复,感情深挚。5、《哀郢》:(见后),作于(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克郢都之时。6、《涉江》:(见后),作于《哀郢》后。7、《悲回风》:作于接近衰老之年,通篇抒情而很少叙事,其诗题取自篇中首句“悲回风之摇蕙兮,心怨结而内伤”,全诗写了朝廷群小对自己的迫害。诗中以独白的口吻,感时伤物,由物及人;其感情的基调是哀怨、孤独、彷徨;诗中多用双声叠韵联绵词,极大的增强了节奏感和音乐性;成为宋玉《九辩》一诗的鼻祖。8、《怀沙》:作于诗人临近自沉,其诗题取自“伤怀于长沙(汨罗江)”之意。全诗表达了诗人在极端困厄中,面对沉冤莫伸、国无宁日,进谏无路已无可为之时,从容赴死的决心。9、《惜往日》:是诗人的绝笔,是他的最后一篇述志诗,其诗题取自篇中首句“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惜,痛惜;往日,指曾被楚怀王信用的日子。在《惜往日》中,诗人追忆了自己早年的政治活动,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功败垂成的经过,当初自己曾倍受楚王信任,受命颁诏改革时政,却因身遭迫害,失位被疏,改革流产,诗人在“弥留”之际重申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充分表明这不仅是诗人一生命运的转折,也是楚国命运的转折点;诗人指责楚国当政统治者任私枉法,误入歧途,就象骑马奔驰而无缰绳,急流行船不备船桨;全诗最后说“宁溘死以流亡兮,恐祸殃之再有”,表明诗人之死是既殉于志,又殉于国,崇高而悲壮,千古之下,令人无限痛惜、景仰。四、定位:1、屈原的《九章》,与诗人的《离骚》《天问》等作品不同,它写作于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时间跨度很长,因此,其表现的思想内容和风格也不尽一致。2、《九章》的各篇作品,客观的表现了诗人一生每一阶段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是诗人平生遭际之印证。3、从思想内容说,《九章》各篇与《离骚》一样均为政治抒情诗,除少数篇章的少数片断采用幻想、夸张外,主要是纪实之辞,其内容的悲剧性和感情的真实性,读之裂人心肺,催人泪下。5、《九章》语言十分生动精妙,工于抒情。6、《九章》篇章结构随着诗人感情而跌宕起伏,有时激情澎湃,有时凄苦低吟,有时缠绵悱恻;有如江流河涌,有浪蜂也有波谷,有平缓也有陡峭;诗人感情的节奏形成了诗歌内在的节奏。
第二节《九章》作品研读一、《橘颂》:1、原文:后皇嘉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緼宜修,姱而不丑兮。嗟而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2、释题:《橘颂》是诗人早期创作的四言体为主嘉美楚地特产橘树的拟人化咏物诗。3、内容:A、前六句为第一段,总体上高度赞美“橘树”“受命不迁”的伟大,实际上也在托物自况,借橘的“受命不迁”抒发了自己的宗国只情和乡土之恋,并为自己生于楚,长于楚,义不去楚的伟大情操,树立了美范。B、从“绿叶素荣”到“姱而不丑兮”为第二段,全力赞美橘树的叶绿花洁,枝茂果圆。即内美外修,文采斑斓,语含双关,有诗人自己的形象在“亮相”,即充满了对内美外修非凡人格的自颂自矜和自许。C、从“嗟而幼志”到“参天地兮”为第三段,集中展示了橘树的五大崇高品格“异志”:独立不迁,廓其无求,横而不流兮,终不失过,秉德无私,以橘树自况,借物言志,托物寄情,浑然一体,比前一段更明显,更深入。D、最后八句为最后一段以橘树为友为师,守志之心更加坚决,最后提出以伯夷为榜样,表明自己不仅有乡土情怀,更有以死报国的初衷。4、意义:A、《橘颂》是屈原现存作品中最早的一篇,也是一篇重要的明志之作。B、《橘颂》中的人格精神成为后来《离骚》之长江大河的最初的一股潺潺清泉。C、《橘颂》通过对橘树拟人化自况化的高度赞美了爱国、无私、自慎、好修等崇高品格。D、《橘颂》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也最为成功的一首咏物诗成为我国咏物体诗的具有“永恒魅力”的范本。二、《哀郢》:1、背景:《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克楚国都城郢都(今湖北江陵),当时楚王仓皇东迁,百姓(生民)背井离乡,四处流亡,惨不忍睹,屈原百感交集,写下了这篇哀歌。2、释题:“哀郢”即是哀悼郢都的沦亡。3、内容:A、诗歌开头描写了郢都百姓因战乱而四处逃亡的惨乱景象。B、中间描写诗人自己离郢都时对故都的难舍和系念以及国破家亡的无限悲哀,C、对统治者祸国殃民的罪行进行了痛心疾首的揭露和批判。D、结尾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诗句,无比深情的表达诗人至死不渝故都之恋,深挚的故国之情。4、意义:《哀郢》是伟大诗人一篇沉痛哀痛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纪实之作。全诗紧扣“哀”字,--百姓流离失所之哀,步步怀思之哀,回归无日之哀,可谓事事刺心,步步生哀;诗中多用呼告,感叹句,词悲情痛,裂人心肺,深刻的表达了诗人的爱国情怀。三、《涉江》:1、背景:作于《哀郢》创作之后,此时,诗人已流放江南,人生的晚年。2、释题:因诗中着重记述了诗人渡江而南,浮沅水西上的历程和心情,故名《涉江》。3、内容:A、诗的开端采用浪漫主义手法,淋漓尽致的表现了自己的苦闷和欲忍不能的凄楚。幻想自己既然不被污浊的黑暗的现实所容,就干脆“高弛而不顾”——飞龙在天,天马行空,去寻古帝重华(帝舜)同游于天,以至“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B、接着诗歌以纪实之词具体叙述了自己被流放的地区和途径行程:他渡江后,经过鄂渚(湖北武昌),到达洞庭湖地区,然后上沅水西行,经过枉锗(湖北常德)、辰阳(今湖南辰溪),入溆浦(今湖南溆浦),独处于荒僻的深山之中——这是诗人晚年被放逐生活中一段最凄苦的行程。4、意义:全诗塑造了一个光明正大,执着不阿的“与日月同辉”的爱国者形象;表现了“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的矢志理想,决不屈服的无私无畏精神;这是有关诗人晚年被流放所经历地区的一项重要史料。
第六章具有神话色彩的优美抒情组诗《九歌》第一节《九歌》概述一、写作时间:《九歌》大部分篇章作于屈原被流放到江南之时。其中《河伯》《国殇》可能作于自疏于汉北的时候,《九歌》的编辑可能是屈原在流放于江南的艰难岁月里进行的:经过整理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二、释名:《九歌》是屈原吸取楚地民间神话故事,利用民间祭歌形式写成的意象柔媚,情感缠绵,语言优美抒情诗集,包括十一篇作品;“九歌”之名,来源于“九天”,古代传说上天有九重,故称天乐为《九歌》,神话传说中,大禹的儿子夏侯启,曾三次上天,窃取天帝之乐《九歌》,从屈原的《九歌》看,大部分篇章取材于神话,写了诸神故事,袭用古乐《九歌》之名,也是很自然的。三、篇目:现存《九歌》共有十一篇:《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歌》中的神灵可分为三类:1、天神:天之尊神(东皇太一),日神(东君),云神(云中君),寿神(大司命),子嗣神(少司命)2、地祗:(qi)湘水神(湘君,湘夫人),河神(河伯),山神(山鬼)3、人魂:将士魂(国殇)四、释题:把《九歌》定位在为哀悼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而作的具有民俗性的爱国诗篇,固然显示了对《九歌》的看重,但并不符合它的实际,因此也是不能接受的。把《九歌》的一首首优美的抒情诗“泥定”为是由扮演各种角色的神巫的唱词,无疑会削弱其优美的意味,也是不能接受的。五、《九歌》的艺术成就表现在:(1)拟人化的自然神形象的塑造,诗中各类神的生活环境、容貌体态,都与其自然物的特点相合;诗人同时又赋予了它们人的特征、人的性格。(2)情景交融的意境,作者善于把周围的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感情融合起来,(3)情味悠深的语言,它往往十分单纯自然,但又非常优美、极富含蕴。第二节《九歌》作品研读一、《东皇太一》1、释题:把“东皇太一”定义为天之尊神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作为一个完整的祭礼仪式,不可能一上来就祭祀某一个神灵,必然要有一个迎神仪式,《东皇太一》即迎神曲。至于为什么叫作“东皇太一”,可能的原因:一是古人有以东为大的观念,二是楚人认为自己是在秦国的东方,三是“太一”即至高无上的意思。2、内容:《东皇太一》一开始写人们在特选的吉日良辰,以十分敬畏的心情,集合起来,准备举行一场场面恢弘,气氛隆重的祭礼。接着典礼开始了,主祭者——一个繁饰盛装的巫师出场了,他身携长箭,腰佩美玉,且一举一动之间,好不恭谨,好不严肃。“瑶席兮玉镇”以下,四句,写的是摆在祭坛上的供物。瑶席、玉镇,显示祭礼的隆重和典礼的规模,馥郁的香花,精美芳香的祭肴祭酒,,即表现奉献者的美意,也显示着受享者“神格”的高洁。随后就是竽、瑟齐鸣,纵声歌唱,强烈的表达了对神灵的颂赞敬慕之情。接着一群男女巫师,身着光彩照人的盛装,手持香花,在祭堂前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翩翩起舞,香风四溢,在五音交会,繁声四起中,一场隆重的祭祀典礼结束了。3、意义:一方面让人感到天神在安享了丰富高洁的祭品和人们的普遍颂赞以后,觉得心满意足,进而使下界的人民也会广受福荫,获得保佑;一方面使人们在观赏楚楚动人的乐舞的同时,随着诗中对祭礼进程的描写,感情起伏,并最终得到了一次上帝的祝福,对生活的美好未来,充满了憧憬。二、《东君》1、释题:《东君》是一首对日神,即太阳神的颂歌。“东君”为日的别名,亦是尊称。日出于东方,故有“东君”之称。
2、内容:《东君》把旭日东升,到日丽中天,最后到日落这一自然景观象征性的幻化为日神的出现,除暴安良,直至杳然离去的祭祀过程。先写日神的出场,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投射出最初的一缕阳光,——黑暗开始退去,大地一片光明,然后写日神东君升天时的显赫声势和暂离所居的心情;霞光万道,熠耀长空,若彩旗迎风飘扬;吞吐浮沉于云气之中,乍升乍降,仿佛一个行将远行的游子,去而又低徊顾怀;紧接着祭典上娱神的歌舞可是了,先是琴瑟张弦,既而鼓声大作,钟声轰鸣,与此同时,篪、笙鸣响,奏出悦人心神,令人陶醉的美妙音乐;一群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少女,翩翩起舞,她们那轻盈婀娜的舞姿,象翠鸟般飞转盘旋,于是展诗诵章,群体合舞。这时满台的歌舞,已经将日神团团围住,群情高涨,热闹非凡。在受到如此的拥戴后,日神开始履行他为民除害的壮举,只见他青云为衣,白霓为裳,高举起长弓大箭,奋力射向肆虐的西北“天狼”,天狼星应声而坠,人间天上皆大欢喜,日神于是以北斗为酒杯,挹桂浆痛饮,庆贺诛暴取得的胜利。3、《东君》是一篇神话歌舞诗,其中射天狼的细节,应是具有象征消灭“虎狼之秦”的寓意;“东君”作为日神的化身,是人们对辉煌的自然天体——太阳的拟人化审美想象的产物,尤其是日神身着青云、白霓,手持长矢,勇武无畏,恰恰是行于高空,光芒四射的太阳的审美想象的结晶;诗人对太阳神英雄性格的倾情塑造,寄托了他的报国之思,爱国之情,同《国殇》一样都饱含英雄主义精神,表达了诗人的爱国情怀;与其说颂神的祭歌,不如说是寄托了诗人理想的对光明、对正义,对英雄性格的礼赞。三、《云中君》1、“云中君”一般认为是“云神”,但古代文学中,尤其是早期文学中直接歌颂“云神”的几乎没有,而且能给人们带来甘霖的“云神”,通常也绝不象《云中君》描写的那般美丽,华贵和缠绵。因此,“云中君”还是应该象姜亮夫先生主张的那样,是颂扬“月神”的,“与日月齐光”是不能成为把“云中君”认定为月神的障碍。2、《云中君》写到:月神在经过了芳香的洗浴后,又穿上以鲜花装点的五彩仙衣,成为象美玉一般纯洁无暇的仙女,光华四射,又威严无比,飘然而降临,接受人们无限美好的祝愿和神情,然后月神离去,留下了无限的留恋。3、全诗热情礼赞了月神的功德,表达了人们对月神的真挚而纯洁的感情,诗中对月神的形象和心理刻画非常成功。四、《大司命》《大司命》一般认为是楚地祭祀“寿命”之神的乐歌,诗中刻画了一位神通广大,威武严肃,使人感到神秘而敬畏的生命之神的形象,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生命的神秘感,和极为关注的心情,表现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清醒乐观的人生态度。全诗在结构安排、形象塑造和气氛渲染等方面,都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造诣。五、《少司命》1、释题:关于“少司命”的含义,历史上曾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说法:一是主子嗣,即送子娘娘或送子观音;二是主男女情缘,即民间所谓“月下老人”;三是主灾祥,即西方所谓“命运女神”。我们认为:司命应该是主管人的生命、命运的神祗;司命又分为两种,一是大司命主生死,或偏于主死,主寿终;少司命则主生,即对生命的保护和福佑,是使生命由幼至长不受戕害的保护神,也是去灾呈祥的神。2、内容:诗中写少司命(应为男性)在芳香素雅的氛围中出场了,秋兰、蘼芜、罗列满堂,绿叶素枝,白花吐蕊,阵阵香气,沁人心脾;在热切的企盼中,少司命飘然而至,没有威风凛凛、没有容光焕发,却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愁苦模样,引起了人们无限的关爱,表达了人神之间的绵绵情意。——在倾情迎神的众多美女中,少司命“忽独与余目成”,这位美女真可谓是亦惊亦喜,异常自豪。但接下来便是匆匆而别,“入不言兮出不辞”,悄悄地来,又默默地走了,这对那位被他所恋,同时也恋他、爱他的美丽女子来说,未免太缠绵,太凄迷了:“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之后便是别后的无限向往和失意。“君谁须兮云之际”恰恰是着眼于那位痴心女子的惆怅心理。“与女游兮九河”四句,是一种向往,甚至是一种幻觉似的白日梦;诗的结尾,对少司命华美高贵的身份和威仪以及作为人类守护神的使命和尽责进行了热烈的礼赞,高度的信赖。3、意义:“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目成”,极其生动地写出了两心相悦、眉目传情的男女(恋人)之间(审美的)心招目挑深情蜜意,心灵交会的爱情交流场面,正所谓“曲尽丽情,深入冶态”;“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极为简练,深刻,动人,从而被古人推许为“千古情语之祖”;表现了对少司命“荪独宜兮为民正”的独一无二、非他莫属的无限颂赞和无限的信赖。六、《河伯》
1、释题:“河伯”即“河水神”,也即黄河之伯,就是黄河水神;《河伯》是取材于河伯神话故事写成的一对水神情侣的一段恋情故事,他们相聚出游,复又执手相别。《河伯》所写是河伯、洛神神话故事的一个片段。2、内容:《河伯》全诗可以分为:同游九河,幽会水殿,美别南浦三个层次。龙螭为驾,河盖饰车,河伯携情侣洛神,在水面疾速奔驰,莽莽大河,蜿蜒千里,他们逆流而上,直至河源,这是一幅令人无限神往的壮美场面,也表现出水神河伯手携情侣洛神倾情出游中那种欢快愉悦弥情天地,不可一世的浪漫情态;但当他们登上昆仑之时,却若有所失,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家,于是他们想起他们的“极浦”,即温馨的“龙堂朱宫”。于是河伯、洛神双双来到水中宫殿共度只属于他们的良宵:鱼鳞砌成的龙堂,闪烁着晶莹的亮光,画壁的龙纹,令人神夺目眩,再加上紫贝、朱红的色彩,显得是那么神异而美丽。然后河伯伴着洛神在水上嬉游而下,分别的时候到了,“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这对爱侣也要在“南浦”暂别了,临别之际,河伯紧紧牵着洛神的手,难舍难分,正所谓“相见时难别更难”但美人随从已至,终于不得不告别了。3、意义:以极其优美的笔触描写了屈原时代一个充满无比情爱的情爱过程;由于“南浦送别”的场景写得极为动情,以至“南浦送别”成了后世叙写离情别绪的生动典故。七、《湘君》《湘夫人》1、释题:储斌杰先生把《二湘》看成是一个恋爱故事,以及认为二者写的都是相思、相疑、相约、又得不到相会一是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二是二者是回环复沓。这是不能接受的。——其实,《二湘》应该认定为是以虞舜和娥皇、女英的动人传说为素材的缠绵凄美的恋歌。湘君,湘夫人分别是虞舜和娥皇、女英幻化而成的湘水配偶神,由于传说素材的原因,湘君,湘夫人被写成彼此热烈相爱而终于未能相会,但却体现了楚人对湘水的深厚感情,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沉的爱情美满的强烈期待。2、内容:《湘君》以湘夫人为主角,写她乘兴赴约,等候湘君不遇,为情所伤,直至绝望的心路历程;《湘夫人》以湘君为主角,同样写他应湘夫人之约前来赴会,并精心的作了各种准备,准备筑室同居,充分享受爱情甜蜜:为迎接佳人的到来,他在水中筑起了新房,用荷叶做屋顶,用香草紫贝修砌墙壁铺垫庭院,厅堂中撒满香椒,用桂木作梁,木兰为椽,辛夷木的楣用白芷花做装饰,薜荔枝叶编成帏帐,惠草做隔扇,用白玉镇席,把石兰花散播到各处散发芳香……总之,一切都无不精美绝伦;另外,他还想象有九嶷山的众神,前来迎接簇拥她进入洞房。门但终因不可知的原因,一切化为痴心幻觉。3、意义:《湘君》《湘夫人》是《九歌》的代表性作品,对新居的精心构筑,反映着居于秀山美水的湘水神所特有的审美趣味,也正表达了他对爱情的珍视,宾至如归的场面,更表现了他所强烈向往的幸福感;诗人对其中的爱情悲剧表现了无比的同情,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无限向往和无限期待,体现了楚人对自己历史文化的深厚感情。八、《山鬼》1、原文: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谁华予!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伥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貁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2、释题:《山鬼》写山中女神的恋爱故事。“山鬼”未称“君”“伯”等,不应使人联想到精灵鬼怪以至人之鬼魂,因为古代鬼神二字意义是相通的。至于“山鬼”所指,一般认为是传说中的巫山神女瑶姬,但也可以认为是泛指山中女神。3、内容:《山鬼》是按照女主人公“山鬼”
出场赴约,等待相会,失望痛楚这样三个层次来写一个凄迷的爱情故事。首先写山中女神的出场,她穿着华丽芬芳,容貌更加秀丽可爱,两目含情,笑脸盈盈,体态窈窕,充满青春的朝气和少女的魅力,她正热切的期望着被恋人所欣赏、爱慕和倾倒;然后写到女神来到约会地点,却未能象热切期待的那样见到爱人,其焦虑凄楚可想而知。最后,虽然女神的意中人最终也没有来,但对幸福的无限憧憬和对对方的一片痴情,她不愿或着本能的拒绝去想自己的可能被抛弃,她还是在为对方开脱;在夜幕降临,雷声滚滚,大雨滂沱,猿声凄厉,落木萧萧的天幕下,女神孤寂无告,在极度哀伤忧愤之中结束了全诗。4、意义:在屈原的艺术加工下,山鬼这位山中的精灵,成为既是自然美的化身,又是一位多情的少女,她空灵飘渺,仪态万方,同时又多情善感,有着贞洁的品格和无限丰富的内心世界。在《九歌》中的诸多神祗中,山鬼是塑造得最美的一位女神。九、《国殇》1、原文: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桴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携秦弓,身首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2、释题:《国殇》一般认为作于江北,“殇”是指“非善终者”,即夭折者,在本篇中即指战死者;国殇,即是为国战死者,捐躯国难者。3、内容:《国殇》以激越的感情,壮烈的战斗场面描写,深情讴歌了捐躯国难的楚国将士们的威武不屈的伟大魂魄:《国殇》一开始(前四句)就描写了一场战斗的悲壮,以及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预示着这场战斗的残酷和惨烈以及失败的结局。接着(中间十句),具体逼真的描述了战车相摩,旌旗蔽日,箭如雨发,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楚国将士明知敌强我弱,但毫不气馁,个个争先恐后,冲锋陷阵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搏斗,直战得天怨神怒,弃尸遍野;——终因力量相差过于悬殊而败下阵来,但出国将士以及主帅却表现了义无返顾、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和浩然正气,他们至死不肯放下武器,即使身首异处也不屈服。最后(最后四句),诗人以极大的敬意无限深情的礼赞了捐躯国难的出国将士。4、意义:《国殇》描写了一次失利的战争,但写得激昂壮烈,正气凛然,充满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诗中为爱国者树立了英雄群像,读来令人敬仰,激人心志。十、《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1、释题:把《礼魂》说成《国殇》的“乱辞”是很牵强的,《礼魂》还应该解释为祭礼告成的送神曲。2、内容:刚一宣告礼成,便鼓乐齐鸣,汇然而起,众位妙龄美女手持鲜花,互相传递,翩翩起舞。同时,动人的歌声婉转缠绵,悠扬不绝。其热闹纷繁的气氛,五彩缤纷的场面,令人宛如耳闻目睹,身临其境。结尾两句用春兰,秋菊来形容季节岁月的更替,兼寓时光的美好以及心愿的洁诚,“长”、“无绝”、“终古”三个近义词,一层深一层,组成一句,强调地写出一种虔诚和期望的感情。3、意义:《礼魂》通过描写祭礼结束百乐齐奏,群歌群舞的热烈场面,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绵延无绝进行祭祀的虔诚愿望;只有短短的五句,二十七个字,便把当时的热闹气氛和人们虔诚的心愿完全表达出来了。
您可能关注的文档
- 九年级语文下册第五单元17屈原课件新人教版
- 九年级语文下册第五单元17屈原(节选)习题课件新人教版
- 教案:屈原与端午节
- 大班语言:屈原沉江.doc
- (全国通用)中考历史专项练习中国古代史中华文化的勃兴屈原与战国编钟(含解析)
- 乐平里屈原故里文化旅游项目可行研究报告
- 浅谈屈原故里十大特色端午习俗原汁原味展现
- 爱国思想汇报 屈原
- 端午节屈原资料大全
- 高一语文屈原列传教案设计
- 端午节缅怀屈原演讲稿
- 怀念屈原朗诵稿
- 高中语文 15 屈原列传(节选)优化设计 大纲人教版第6册
- 高中语文 2.3《屈原列传》教案 鲁人版必修3
- 高中语文 屈原的离 骚教案 新人教版必修2
- 高中语文《屈原列传(节选)》教案1 苏教版选修《史记选读》
- 高中语文《屈原》教案1 苏教版选修《中外戏剧名作选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