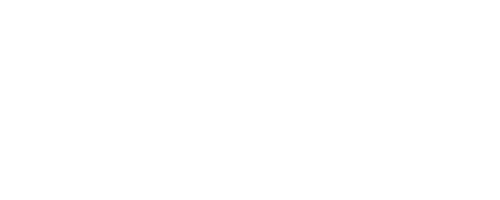- 48.00 KB
- 2022-06-16 11:50:08 发布
- 1、本文档共5页,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可选择认领,认领后既往收益都归您。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先通过免费阅读内容等途径辨别内容交易风险。如存在严重挂羊头卖狗肉之情形,可联系本站下载客服投诉处理。
- 文档侵权举报电话:19940600175。
sunshine从“小红帽”的三个故事版本谈结尾的意义孙尚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摘要:本文以贝洛版、格林版的《小红帽》和芭芭拉·G·沃克的《小白帽》三个故事作为版本取样,主要采用罗兰·巴特的可读性和可写性的理论,对源于同一故事的不同结尾的意义进行阐释,认为结尾的差异关乎文本对读者的定位,并且进一步探讨了结尾的可读与可写的相对性问题。同时对结尾所含的意识形态也做了简单的分析。关键词:小红帽;结尾;可读性;可写性;意识形态“小红帽”的故事随着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改写,这些改写的版本,不仅表达的方式各有差异,所含蕴的意义也不尽相同。从凯萨林·奥兰丝妲(CatherineOrenstein)的论著《百变小红帽》,我们大抵可以知道小红帽的故事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演变。这些变异的故事有着不同的结构,更有不同的结尾。从结尾来探索小红帽故事的变异性,似乎也就成为一个可加以选择的课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可读性与可写性的角度来谈小红帽故事结尾的意义。本文只选取三篇作为样本来分析,即贝洛版与格林版的《小红帽》和芭芭拉·G·沃克(BarbabaG.Walker)的《小白帽》。取样虽然有限,但是就其结尾来说,我们仍然可以从三个版本看出一些明显的问题。一 《小红帽》的文本结构及其结尾《小红帽》这个看似简单的童话故事之所以引起如此多的关注,产生如此多的版本,与它的结构关系颇大。阿尔奈《民间故事类型》说:“任何类型的故事都可能有数不尽的变异版,以致故事源源不绝。好比更换主角的服装,随即产生新的主题,却没有改变故事的主结构。”[1](p.267)《小红帽》的衍生正符合其所说的情形。以下,我们先以普罗普的叙事学理论来梳理一下贝洛版和格林版的《小红帽》叙事结构:1缺席:小红帽从家里面出来去外婆家2禁止:小红帽的妈妈告诉小红帽不要走小路3违背禁令:小红帽没有听妈妈的话跑到路边去摘花4侦察:小红帽遇到野狼5弃守:小红帽同狼说她要到外婆家去,并把外婆家的地址告诉了狼作者简介:孙尚前(1981-),女,辽宁朝阳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现当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方向。sunshine
sunshine6欺骗:野狼假扮成了小红帽到外婆家去敲门7共犯:外婆相信了狼,让它进了屋子8恶行:狼吃掉了外婆和小红帽9神奇的援助:猎人在外婆家的门外听到狼的声音,进去剪开了狼的肚子10起初的不幸获得补救:小红帽和外婆从狼肚子中跳出来11恶棍受到处罚:狼被肚子里的石头压死这是一般所接受的小红帽故事情节,几乎所有的改编都是从这个结构入手的。从上面的功能分析来看,《小红帽》的结构是有“空白”的,而这个结构的“空白”中止了本文模式的联结,把读者引到“填充”的行为上来,为读者的改编提供了可能性。再者,小红帽的结构是一个可以套进许多故事的自由度较大的结构,即在主结构不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变换人物的行为重新组合故事。前者可以以格林版的《小红帽》为例,这个版本的结构是在贝洛版本的功能上增加了几个功能。在“缺席”与“侦察”中加了“禁止”与“违背禁令”两个功能,在“恶行”后面加了“神奇的援助”、“起初的不幸获得补救”、“恶棍受到处罚”三个功能。而这几个功能的增加不只是改变了结尾,也使《小红帽》完全改变了原来所要传达的观念。后者可以《小白帽》为例。《小白帽》的结构与贝洛版的是完全相同的,只是其中的内容已面目全非。它述说了一个巫婆外婆和她的孙女小白帽如何惩治猎人而替狼族报仇的故事。在故事中,小白帽不再是一个甜美娇小的小女孩,狼也不再是凶恶无比的狼,反倒原本作为援助者角色出场的猎人与外婆共同分担了狼原来的角色。猎人替代了与小红帽相遇的狼,而外婆则替代了吃掉外婆和小红帽的狼。也就是说,在这个版本的结构功能中,“侦察”功能已变为小白帽与猎人相遇,“弃守”变为小白帽让猎人知道了外婆是谁,“欺骗”功能变为外婆扮成凶恶的狼,“共犯”功能是猎人被骗进门,“恶行”是外婆把猎人杀死并把其身体斩成小块喂狼。这种大幅度的内容变动必然导致结尾大异于原版。小红帽故事三个版本的结尾都不同,而这种不同不只暗含了创作者的意识形态,并且对读者的接受也产生极为不同的效果。现在就从可读性和可写性的角度来对三个版本的结尾进行分析。二 从《小红帽》到《小白帽》:结尾的可读性与可写性可读性与可写性是法国著名的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在《S/Z》中提出的概念。屠友祥译之为“能引人阅读者”和“能引人写作者”,这种译法可以作为理解上的参照。巴特在《S/Z》中写道:sunshine
sunshine启程/旅途/到达/居住:旅程被一一填满。使之结束、充满、接合、统一,这可以说是能引人阅读之文的基本要求,其惶惶然,似慑于某类挥之不去的恐惧:省却某一环节的恐惧。惟恐遗漏,遂产生出情节的逻辑外表:各项以及其间的衔接得到安排(结撰),以便交互合并、重迭、创造某种连续性的幻觉。充盈导致描画,以‘表现’此充盈,而描画又引发补苴罅漏,一一着色:能引人阅读之文仿佛憎厌空白。[2](p.197)从以上这段话可以了解,可读性的文本是一个统一而和谐的整体,它采用“面面俱到”的方式力图使文本成为一个“固定的自足的现实文本”,并且把文本的意义明确地传达出来。“在可读性文本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文本的意义是可以把握解读的”。[3](pp.368-369)它厌恶“空白”的特点,使得它拒斥读者的重新创造。一个文本若想吸引读者对其再创造,“空白”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文本的“空白”对读者来说是一种召唤的方式。根据伊瑟尔(WolfgangIser)的说法,“空白”与“否定性”是本文与读者进行交流的基本条件,“空白自发地调动了想象,提高了读者的建构能力,他不得不尽力补充空白,把这些本文图式联系起来,成为综合的完形。”[4](p.238)可读性文本不只缺乏“空白”,对伊瑟尔所说的“否定性”也是力避其存在的。所谓“否定性”,是对既有的规范的合理性的否定。但可读性文本不会想去动摇读者原有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定势,它是源自文化的而不是与之背离的。一旦把“空白”和“否定性”从文本之中抽离,将导致文本远离“不确定性”,也就阻断了文本与读者的交流。读者在面对文本时只能是接受或拒绝。相对的,可写性文本则隐含着召唤结构,它充满着“空白”和“否定性”,把读者吸引到文本中来,使其打破对世界既有的把握方式和规则,与作者共同创造文本的意义。“‘可写性文本’就是邀请读者从自身的语境中解放出来,而通过偶然或约定的性质,对其所理解的传统观念和符号规约进行反思,从而去探讨对对象的更新的阐释密码。这样,读者就不再是被动地被灌输的群体,而是主动地进行阐释和意义塞入或填入的群体。”[3](p.370)可写性文本令读者“不适”,动摇其阅读趣味、价值观和思维记忆。以上是对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所进行的介绍,以此为基础,现在来谈谈“小红帽”三个故事版本结尾的可读性与可写性问题。贝洛版和格林版的《小红帽》在情节上大致相同,但结尾之一是狼吃掉外婆和小红帽,而另一个是猎人救出了小红帽。从文本结构来看,它们都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结尾与文本的开头和发展是逻辑一致的。不论外婆和小红帽被狼吃掉之后是否获救,狼是否得到惩罚,都是从前面的情节导引而出的。作者对文本意义的预先构想使所有的部分集中投向一个中心点,引向一个方向。小红帽遇见狼并且告诉它外婆家住在哪儿,因此发生可怕的后果,但救助者的出现使小红帽获得拯救且又惩罚了恶狼。一切都顺理成章,结尾既没有留有想像的“空白”sunshine
sunshine,也没有对读者的原有价值规范有所否定,相反的恰恰是对传统道德与价值规范的强化和肯定。因此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可读性结尾。如同《S/Z》中所说:“能引人阅读者的道义法则、价值法则,处于充满因果链的境地;由此看来,每个决定物(determinant)在可能的范围内必须是被决定物(determine),这使得每种表示(notation)都处于居间状态,被双重地定向,卷入朝向目的的航行中。”[2](p.294)也就是说,在可读性文本,结尾是文本结构自然发展出来的一环,它并没有逃逸出读者所期待的视野。作为女性主义颠覆书写的《小白帽》,其结尾是一个可写性的结尾。(这是相对于传统版本来说的。其实相对于这个文本的前面情节来说,这个结尾也是可读性的。详下文。)这个文本借用传统小红帽故事为背景。依照伊瑟尔的说法,入选的现实和社会规范作为本文的前景并没有消除被淘汰的规范,只不过这被淘汰的规范已退居为背景。经由前景与背景的对比,读者对本文有了全新的理解。[4](p.14)我认为结尾也是同样的情形。《小白帽》的结尾潜在地预设了读者知道《小红帽》原版故事的结尾,而且是接受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群体。如此一来,《小白帽》的结尾才能以不受传统束缚的方式打破读者的期待,提供读者以一种陌生的乐趣,并对读者原有的价值观念,性别意识和道德观提出挑战。《小白帽》的结尾是:幼狼被很好的救护,猎人被杀死以喂狼,而杀死猎人的竟是外婆,小白帽则把这件事轻描淡写讲给妈妈听。这种结尾是以“否定性”的方式引发读者对文本的参与创造。读者对这个结尾想必会有一种心理上的拒斥感,有一种“不适”,不太能接受小女孩和外婆的残忍。随后,读者会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尾,当他意识到这是女性主义的颠覆书写,是一种极端化的反叛,他就会对自己原有的各种价值规范进行反思,从而对文本有全新的理解,而对原有的观念重新调整和定位。读者不再会想当然地把小女孩定义为天真无知,不再会想当然地把男人视为正义的化身以及拯救者的象征,狼也不再一定是凶恶的,而外婆也拥有自救的能力。女性不一定非要男人保护,狼不一定比人更残忍。当他返观原版《小红帽》时也不再会把其中的情节作为想当然的事来接受,他就会看到其中浓厚的意识形态(男权意识、人为中心的道德观)在过去是如何以“伪自然”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这样结尾促成了读者积极参与文本的生产,也完成了读者与本文交流的目的。然而我们必须强调一点:可写性结尾与可读性结尾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对一个人来说是可读的对另外一个人可能是可写的,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诠释系统都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对一个熟悉女性主义颠覆文本并对其结尾形式已有一种定势思维的读者来讲,读《小白帽》时很可能就不会把它结尾当作是可写性的。“每一种语言一旦被重复了,即顷刻成为旧语言。”[5](p.51)结尾也是如此。而对于从没有读过这种文本或极少有此阅读经验的人来说,这个文本的结尾则是可写的。此外,对一个人来讲,一个文本的结尾是可读还是可写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当他熟悉一种可写性的模式以后,再返读最初读的此类文本时则已是可读的了。sunshine
sunshine结尾的可读与可写还涉及一个问题:是以版本作为参照?还是以文本的背景作为参照?就《小白帽》而言,先前我们说它的结尾是可写的,那是相对于传统版本来说。要是相对于这个文本前面的情节,它的结尾则是可读的。不管是男猎人的死,小狼的被救,还是外婆的自救,这在前文都已做了足够的铺垫。例如故事前半段交代外婆对动物特别好,尤其喜欢狼,这就预示着她将以狼的救护者出现,而和猎人形成对立。又如小白帽,当叙事者叙述她见到可能对她造成伤害的猎人时毫无惧色,这就合理化了在故事结尾时她对杀猎人之事的冷漠。用巴特的话来说,这类文本就是“以一种依逻辑发展的‘桨糊’把所叙述的种种事件粘合起来,话语推行此原则,便臻于着魔的境地。”[2](p.259)《小白帽》的结尾便是这样一步步推衍出来的一个合乎文本发展的结。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到可写性文本不一定就有可写性结尾的推论。 在巴特看来,可写性文本是高于可读文本的。文学的价值不在于表现或解释这个世界而是对这个世界的既有的规范提出挑战,提出更高的意义阐释期待,在于使读者同作者一样成为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在我看来,结尾也是如此。三 故事结尾与意识形态问题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说,“凡业已完成了的语句均要冒成为意识形态之物的危险。”[5](p.61)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在结尾的理解。在文本表层理所当然的表述之下,都有一种深层的意识在支撑着。因此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就需要从表层深入地去探求它所蕴含的深层观念。在贝洛版《小红帽》的结尾中,狼把小红帽和外婆吃掉了。依据《百变小红帽》的分析,贝洛版的《小红帽》是一则性爱寓言,在于警告女孩她们的周围潜伏着许多想骗得她们贞操的如狼般的男人。贝洛的《小红帽》捍卫的是他的性道德观。[1](pp.59-60)它的结尾蕴含着整个文本的意含,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这个文本的情节是为其结尾而存在的。格林版的《小红帽》比较明确是写给儿童看的,隐含读者的设置决定了它思想的传达和结尾的安排。它所表达的观念是要小孩子循规蹈矩,要小孩听大人的话,因此在贝洛版《小红帽》的“缺席”与“侦察”之间加了“禁止”和“违背禁令”两项功能的叙事,这样一来,结尾也就自然地显示出它想说的教训意义。此外,这个版本的结尾还增加了猎人救出小红帽与外婆,狼被石头压死的情节。这个情节完全是基于隐含读者的关系而决定的。作者显然不想让小红帽和外婆被吃的情节吓到孩子,因此才添加了猎人的出现。它揣摩着儿童的接受心理,让狼的死法变得很有趣,既受到惩罚又不恐怖。sunshine
sunshine《小白帽》所含的意识形态更为突出。这个故事是女性主义为了批判男权中心论主义而写成的童话,它要突显女性的魅力与实力,揭开男性凶恶的一面。再者,它也表达了保护生态的一种决心,挑战在自然界中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整个文本以女性为中心,表现了她们足以对抗男权、足以自救和拯救自然的能力,并且不认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所以才会有小红帽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来对待她所经历的事情。但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故事的表现也太极端化了,尤其是结尾的处理过于残忍。外婆不仅像狼一样杀掉了人(虽然是恶人),并且还把尸体分成小块给了狼吃,这使得外婆转变为比原版中的狼更凶恶而可怕的角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外婆形象该如何定位呢?女性主义力图推倒一个权威,但推倒的目的难道是再建立一个只是换了性别的权利世界吗?这种结尾的安排显然有矫枉过正的嫌疑。“童话故事宛似一个生命体,随着时代背景、权利及经济结构之变迁而改变,其主题为配合时代的现实,会产生无数的变异;各种变异版本,则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模式。”[1](p.7)以上三篇童话的结尾也一样,不同的结尾反映了不同的社会道德,性别意识等的变迁。我认为,这种变化正代表着童话从古典走向现代,从可读走向可写。四 结语一个文本不能没有结尾。一个文本有许多可能的结尾。一个文本的结尾或者完全契合读者的期待,让人适意;或者完全破坏读者的预想,诱使人们重新寻找一种内在的和谐;或者,结尾就是另一个开始,使人进入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过程;或者,结尾是无结局的结尾,而把人引向无限可能的幻想。结尾本身不会只为了分类而存在,它只寻找自己存在的可能。这些结尾也许是可读的,也许是可写的;可能是界线明确的,也可能是界限模糊的。不论如何,唯一可确定的是,它们都给读者以愉悦。本文通过“小红帽”三个故事版本的比较,业已论证这就是结尾的意义所在。参考文献:[1]凯萨林·奥兰丝妲.百变小红帽[M].杨淑智译.台北:张老师文化,2003.[2]罗兰·巴特.S/Z[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王岳川.二十世纪哲性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沃·伊瑟尔.阅读行为[M].金惠敏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1991.[5]罗兰·巴特.文之悦[M].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6]芭芭拉·G·沃克.《丑女与野兽》[M].薛兴国译.智库股份有限公司,2000.OntheSignificanceofEndingsfromThreeEditionsof“LittleRedRidingHood”SUNShang-qian(CollegeofHumanities,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Abstract:Thispapertakesthreeeditionsof“LittleRedRidingHood“assamplesandadoptssunshine
sunshinethetexttheoryofreaderly/writerlyofRolandBarthestoexplorethesignificanceofthedifferentendingsderivedfromthesamestory.ThethreeeditionsareCharlesPerrault’sandJakob&WillhelmGrimm’sLittleRedRidingHoodandBarbabaG.Walk’sLittleWhiteRidingHood.Itisfoundthatthedifferencesamongthethreeendingsrelatestothedifferentpositionspreparedforreadersineachtext.thepaperfurtherdiscussestherelativityofreaderly/wrtierlyoftheendingsandtriestorevealtheideologicalfactorshiddeninthem.Keywords:LittleRedRidingHood;readerly;writerly;idoelogy欢迎阅读本文档!suns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