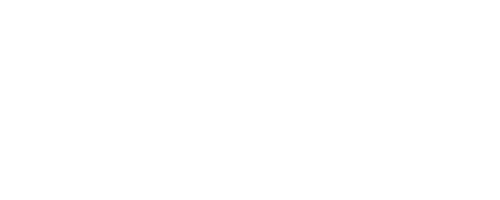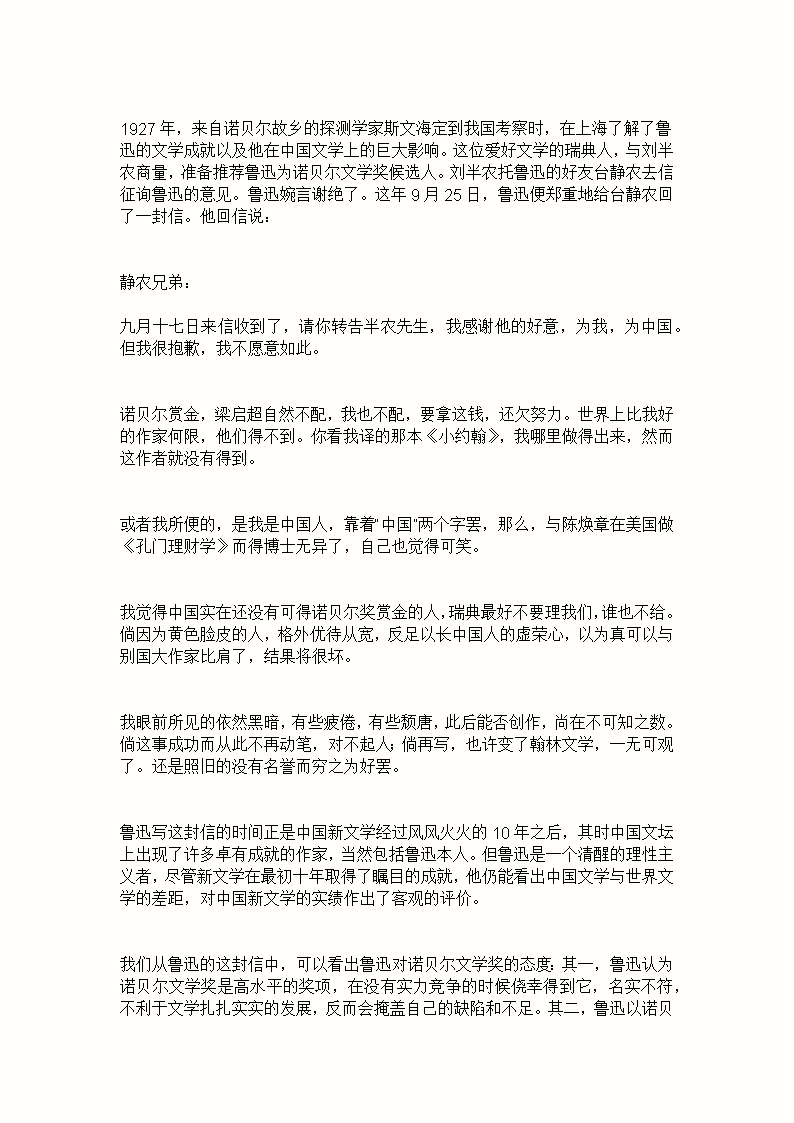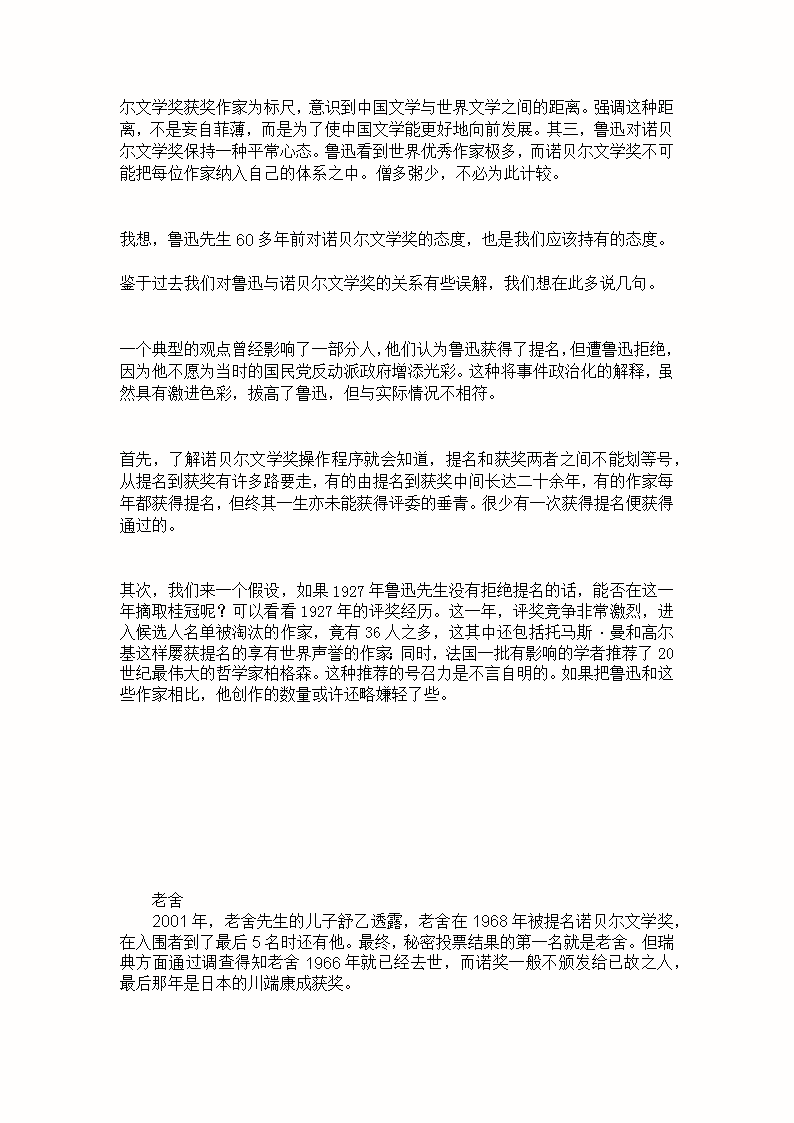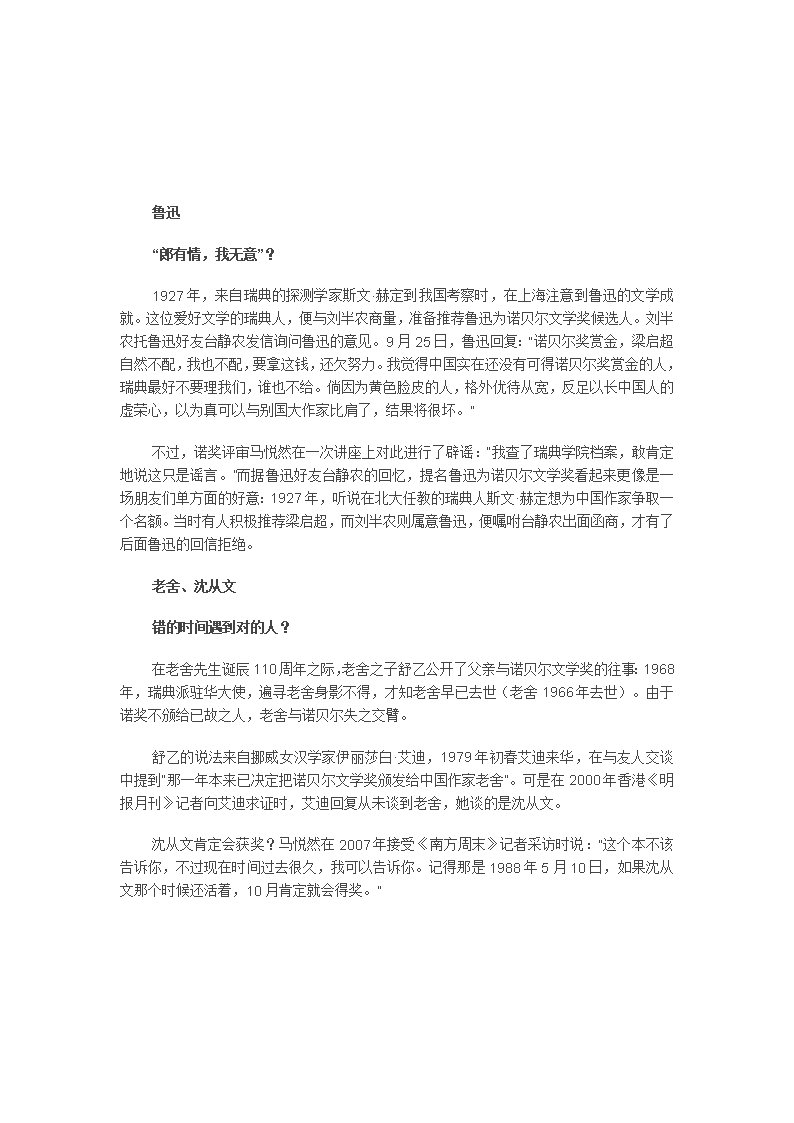- 36.71 KB
- 2022-06-16 11:58:28 发布
- 1、本文档共5页,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可选择认领,认领后既往收益都归您。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先通过免费阅读内容等途径辨别内容交易风险。如存在严重挂羊头卖狗肉之情形,可联系本站下载客服投诉处理。
- 文档侵权举报电话:19940600175。
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婉言谢绝了。这年9月25日,鲁迅便郑重地给台静农回了一封信。他回信说:静农兄弟: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正是中国新文学经过风风火火的10年之后,其时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当然包括鲁迅本人。但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尽管新文学在最初十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他仍能看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对中国新文学的实绩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我们从鲁迅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其一,鲁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高水平的奖项,在没有实力竞争的时候侥幸得到它,名实不符,不利于文学扎扎实实的发展,反而会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其二,鲁迅以诺贝
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为标尺,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为了使中国文学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其三,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保持一种平常心态。鲁迅看到世界优秀作家极多,而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把每位作家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僧多粥少,不必为此计较。我想,鲁迅先生60多年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鉴于过去我们对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有些误解,我们想在此多说几句。一个典型的观点曾经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认为鲁迅获得了提名,但遭鲁迅拒绝,因为他不愿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增添光彩。这种将事件政治化的解释,虽然具有激进色彩,拔高了鲁迅,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首先,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操作程序就会知道,提名和获奖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从提名到获奖有许多路要走,有的由提名到获奖中间长达二十余年,有的作家每年都获得提名,但终其一生亦未能获得评委的垂青。很少有一次获得提名便获得通过的。其次,我们来一个假设,如果1927年鲁迅先生没有拒绝提名的话,能否在这一年摘取桂冠呢?可以看看1927年的评奖经历。这一年,评奖竞争非常激烈,进入候选人名单被淘汰的作家,竟有36人之多,这其中还包括托马斯·曼和高尔基这样屡获提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同时,法国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推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格森。这种推荐的号召力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把鲁迅和这些作家相比,他创作的数量或许还略嫌轻了些。 老舍 2001年,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透露,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在入围者到了最后5名时还有他。最终,秘密投票结果的第一名就是老舍。但瑞典方面通过调查得知老舍1966年就已经去世,而诺奖一般不颁发给已故之人,最后那年是日本的川端康成获奖。
鲁迅“郎有情,我无意”?1927年,来自瑞典的探测学家斯文·赫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注意到鲁迅的文学成就。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便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好友台静农发信询问鲁迅的意见。9月25日,鲁迅回复:“诺贝尔奖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不过,诺奖评审马悦然在一次讲座上对此进行了辟谣:“我查了瑞典学院档案,敢肯定地说这只是谣言。”而据鲁迅好友台静农的回忆,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朋友们单方面的好意:1927年,听说在北大任教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想为中国作家争取一个名额。当时有人积极推荐梁启超,而刘半农则属意鲁迅,便嘱咐台静农出面函商,才有了后面鲁迅的回信拒绝。老舍、沈从文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在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老舍之子舒乙公开了父亲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往事:1968年,瑞典派驻华大使,遍寻老舍身影不得,才知老舍早已去世(老舍1966年去世)。由于诺奖不颁给已故之人,老舍与诺贝尔失之交臂。舒乙的说法来自挪威女汉学家伊丽莎白·艾迪,1979年初春艾迪来华,在与友人交谈中提到“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可是在2000年香港《明报月刊》记者向艾迪求证时,艾迪回复从未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沈从文肯定会获奖?马悦然在2007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这个本不该告诉你,不过现在时间过去很久,我可以告诉你。记得那是1988年5月10日,如果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10月肯定就会得奖。”
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2诺贝尔文学奖第一原则:"作品的普遍价值"。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原则:"作者的洞察力(洋人形容为刻骨铭心)"。诺贝尔文学奖第三原则:"作者的语言技巧(洋人形容为丰富机智)"。诺贝尔文学奖第四原则:"为中文小说和戏曲开辟了新路"。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条件是:诺贝尔文学奖只授给活着的作家。其实评奖的标准是很难说清的,我觉得你到应该先从评奖程序上入手,似乎更能说清楚。我记得某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时候《南周》做了一一次报道,说的很详细。至于为什么中国没有人获得这个奖:最重要的是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被翻译到西方国家的太少,瑞典文就更少了。具我所知,鲁迅先生曾经接到过邀请,但他拒绝了。老舍、沈从文都曾进入过评委的眼帘,但因为过世而没有获得。 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 1968年诺奖评选,老舍得票第一 坊间曾传言,老舍先生曾距诺贝尔文学奖仅一步之遥。“不是传言,是真的。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父亲得票排第一。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奖授予了日本的川端康成。”舒乙向记者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事件内幕。 舒乙认为,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却屡屡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除了政治偏见等原因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和老舍先生同辈作家的作品鲜有被翻译成外文的。而由于老舍先生曾出过国,他的作品有多种译文,甚至连瑞典文都有。1968年,老舍先生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在最终的5个候选人投票中,获得了最多票。“按规定,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该是我父亲,但在1968年,‘文革’已经进入高峰期,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的下落,一直没有得到准确音信,就断定老舍已经去世(老舍的确于1966年8月24日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东方人。结果日本的川端康成就获奖了。” 舒乙告诉记者,已故作家萧乾曾携夫人文洁若到瑞典证实过,老舍在评选中确实得票排第一。(华商)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高建平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事,一方面瑞典文学院的人三缄其口,一方面全世界的文学界都在议论,有人赞扬,有人批评,有人咒骂。中国人谈起这个奖,似乎想说的就更多。中国过去有几亿人,现在又增加到十几亿,有三千年文学史或五千年文明史,为什么这个奖设了长长的一个世纪,竟然就没有一个中国人得到。于是,有人指责评委们有偏见,有人信誓旦旦,要为中国人争口气,更有人说,既然像XX这样的伟人未获奖,或者像XX一样的庸人得了奖,这个奖不得也罢。这样的争论会永久地持续下去。如果有一天,有一位中国作家得了奖,争论不会减少,只会更多。这时,又会有人将得奖者连同评委贬得一无是处,义正词严地指出,某某更伟大得多的人为什么不能获奖,却把奖给了这个X流作家?还会有人出来作“遗憾”、“震惊”、“痛惜”、“无所谓”等千奇百怪的姿态。文学上的事,本来标准就难定,何况,这个奖有着其自身的特点。有人想骂也可以,但是,把情况弄明白后再骂,岂不更好一点?一首先是这个奖的定位问题。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世界文学大奖吗?这一点似乎已毋庸置疑,否则,就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了。但我还是要问:你对世界文学大奖中的“世界”一词究竟怎么看?弄得不好,就可能闹误会。1895年,诺贝尔在遗嘱中规定,用他的遗产设立一个基金,将基金的利息每年“授予那些在过去一年中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其中五分之一授予在文学中“创作了富有理想倾向的杰出作品”的人,“文学奖的授予不强调民族的归属,也就是说谁最有资格谁获得,
不管他是否属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诺贝尔还特别规定,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的文学院”颁发。既然这笔钱是诺贝尔私人的钱,怎么花,就必须遵从他的个人意愿。其实,并没有一个机构的正式名称叫“斯德哥尔摩的文学院”。幸而瑞典国家不大,相关方面的机构还不那么多而复杂。于是经国王批准,遗嘱的这一项就被正式解读为“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并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一个潜在问题:“斯德哥尔摩的文学院”,或者说“瑞典文学院”是否有能力选出创作了“最杰出作品”的人。早在1896年,此议在蕴酿之中时,瑞典文学院的两位院士就出来表示反对。认为这会使文学院变成“世界性文学裁判所”。今天在任的院士埃斯普马克则认为,在这两位反对者的话之上,应该再加一句,“排斥处于领先地位的瑞典作家,并把最杰出的文学研究专家拒之门外的瑞典文学院,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这项敏感的任务。”当然,这句话那两位院士是不会加的,他们是院中之人。此话只有后人或外人才会说。靠瑞典文学院十八院士个人的力量,在全世界的作家中进行筛选,确立创作了“最杰出作品的人”,这显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然而,当时的院士们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选择:要么干,要么把这笔捐赠退回去,从而放弃设立这个奖的机会。而换一个机构做这件事,就违背了诺贝尔的遗嘱。当年的文学院常务秘书魏尔森极力推动此事,他认为,不能剥夺“诺贝尔安排的、使那些长期卓有成效地从事文学活动的欧洲大陆上的文学大师们享受极大的荣誉和利益的机会。”他设想,如果瑞典文学院拒绝做这件可以在“世界文学上取得有影响的地位的工作”,就会受到人们的谴责。他还辩解道,通过做这件工作,从而了解世界文学,对于完成这个机构原来所具有的,评判和推动瑞典本国文学的工作,也会有促进作用。他用这三条理由说服了大多数人,于是,文学院只好勉为其难了。院士们于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这件事,把目光投向了世界文学界。他们所能看到的,当然首先是欧洲,这也是早期的欧洲作家获奖较多的原因。院士们只是对那些通过自己的作品使文学院了解他们的作家作一评判而已。多年来,他们努力扩大视野,注意欧洲以外的文学,注意那些用他们所不熟悉的语言写作的作家,以扩大这种文学奖的世界性。但是,这种关注不能成为一种牵就。他们如果还不能真
正了解用一种语言所写的作品,并对之进行评判,就不能对之作出相关的决定。诺贝尔遗嘱中要求,这个奖“不强调民族的归属,也就是说谁最有资格谁获得”。这是给院士们出的又一个难题。消除地理上的空白点,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到世界各国去,应是院士们的目标。针对许多欧洲作家入选,而欧洲以外作家入选较少的状况,是不是可以改进一下,在各大洲之间来一个摊派?国际体育比赛有在各国或各大洲间分配名额的做法。由于中国乒乓球水平太高,于是,去年获得世锦赛单打亚军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马琳无缘参加今年的奥运单打比赛。相反,中国足球界则希望在各大洲间名额分配的办法会对中国队入选世界杯赛有利。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能不能这么办?一位瑞典籍华人学者黄祖瑜曾试图开一个药方:首先注意不熟悉的语言领域,而后再从中挑出最优秀的候选人。这句话说白了,意思是,像汉语这样的语种,有这么多人说这种语言,有这么悠久的历史,该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了。这个前提可先定下来,再去确定该选谁。这在一些中国作家那里成了一种策略,先喊中国人应该得这个奖,拉来十三亿人做人质,然后自己去“为中国人争光”。记得鲁迅在谈到中国人与诺贝尔文学奖关系时说过,不要仗着黄色脸皮希望外国人“格外优待从宽”,(《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62页。)大概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诺贝尔要“不强调民族的归属”,这几个字解读起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只给欧洲人授奖,是受了民族归属的限制,违背了诺贝尔的遗嘱;另一方面,预先确定要给某个民族授奖,再从这个民族寻找候选人,实际也面临着是否违背诺贝尔遗嘱的问题。当然,民族问题常常会演变成国际政治问题。1896年那位反对文学院接受颁奖任务的瑞典文学院院士想到,这会使文学院变成具有“世界性文学裁判所”。是否被他不幸言中?瑞典文学院能否免俗?多年来争论不休。在东西方阵营政治上对抗时,瑞典文学院努力取一超然的态度。他们承认文学奖会有“政治上的效果”,但坚决反对评选时有“政治上的意图”。用一位院士拉尔西·吉伦斯坦(LarsGyllensten)的话说,他们的指导原则是“政治上诚实”(politicalintegrity)而不是“政治上正确”(politicalcorrect)。将瑞典文学院描绘成“瑞典外交部所属的文学委员会”,是对它最刻薄的挖苦,这是
院士们无论如何不能承认的。于是,想要得奖,打十三亿人,三千年或五千年历史牌,是一张错牌。院士们不能、不会、也不敢吃这一套。如此说来,要使中国人获诺贝尔奖,就必须使他们的作品真正得到院士们赞赏。这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了解中国文学,有充分的信息来源,同时这些文学作品又有优秀的西方语言译本;二是院士们将中国文学作品与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写出的优秀文学作品相比,发现水平够格。显然,这两个条件都对中国作家不利。第一个条件,即信息和翻译:信息量的保有与地理距离成反比,而文学作品的可译性本身就是有争议的问题。翻译家永远是倒霉蛋,替罪羊。“意态由来画不得,当时枉杀毛延寿”。译本只是美人的画像而已,要比美人低一等。第二个条件,要与西方语言写出的优秀文学作品相比。院士们的审美趣味,是在阅读那些优秀西方文学作品后形成的,他们当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与那些作品相比。中国作家心中的理想读者,应是中国人,于是,对怎样的作品才算优秀,有着一个根源于中华的,或东亚文化的评价标准。这种标准并非与西方标准完全不兼容,但也不可能完全重合。其中有着基于共同人性的相通性,也有着出于文化和历史差异的不相通性。中华文化标准与西方文化标准,会构成一种交叉关系。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作家得了奖,那也更可能是由于这位作家作品的趣味处于交叉点上,而不是由于他或她从中华文化的标准看“最优”。从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的角度看,也就只能如此了。中国人看问题讲求“设身处地”,批评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许能想通一些问题。毕竟,院士们只是按照诺贝尔的遗愿,在他们的目光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表达他们的看法而已。如果说,这是一个世界文学大奖,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定位。二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授予创作了“最杰出作品的人”,当然是,诺贝尔的遗嘱就这么规定的。但是,什么叫“最杰出作品”?“杰出”指什么?这里面都有许多解释的空间。诺贝尔的遗嘱中有一个限定语:“富有理想倾向”(inanidealdirection)。这是对“杰出”的一个解释,但随之而来的是新的解释问题。何谓“理想”?怎样的作品才叫“富有理想倾向”?
诺贝尔在写“理想”这个词时,曾作了一个修改。他原来写的是idealirad,这不是一个瑞典语词,其中漏了字母。研究者们认为,诺贝尔心里想的是idealiserad,即“理想化”。然而,诺贝尔不满意“理想化”这样一个在瑞典语中含有“修饰”一类含义的词,因而将之改为idealisk,即将rad改为sk。斯图尔·阿伦教授在经过这一番考证后,联系诺贝尔的一贯思想,指出,这里的“理想”,是一个分类性的形容词,而不是一个评价性的形容词。也就是说,他不是指“理想的文学作品”。在这一表述中,“理想”可能成为“优秀”、“完美”一类评价性形容词的同义词。他所指的是“其方向通向一个理想”(inadirectiontowardsanideal)。用我们的话说,在诺贝尔的心目中,艺术标准并不是第一的,作品的“有益于人类”的效果更重要。诺贝尔奖遗漏了许多重要作家,给后人批评这个奖提供了口实。第一个似乎不该被遗漏而恰恰被遗漏的,也许是瑞典人斯特林堡。斯特林堡在今天已被视为瑞典民族的骄傲,瑞典在世界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对于院士们来说,没有信息传递问题,他与院士们住在同一个城市;也没有翻译问题,与院士们使用同一种母语;更没有文化差异;斯特林堡死于1912年,在诺贝尔奖设立时,他的重要戏剧均已上演,他的广泛影响也早已形成,因而没有时间差。然而,他就是不能得奖,据说连候选人也没当过。瑞典文学院不是不知道他,而是知道得太多了。但一提到他,请免开尊口。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多种多样,有个人关系因素,然而,归根结底还是评价标准问题。这个标准,源于对“理想倾向”一语的解读。在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最初十年里,评奖标准非常强调“不仅在表现手法上,而且要在思想和生活观上真正具有高尚的品德”,要“促进人类朝富有理想的方向前进,扩大人类常规的视野和使其比过去更完美更纯洁。”斯特林堡被这个对“理想”的“高尚”与“纯洁”的解读拒之门外。出于同样原因被拒绝的还有大名鼎鼎的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和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由于勃兰兑斯虽然“对自己的时代具有巨大的影响”,但“并非总是善良的”,而且,他“冷嘲热讽”的语调使他的作品不能使人看到“真切和纯粹的客观性”,于是,他被一些我们今天看来莫名其妙的理由而排斥在门外。至于易卜生,他的早期作品得到了一些院士的赞赏,但由于他的《社会支柱》、《群鬼》和《人民公敌》对社会的批判而使他失去了获此殊荣的机会。在斯堪的那维亚
之外,被否定的还有左拉、哈代和托尔斯泰。否定的原因都与作品没有“理想倾向”或理想不够“高尚”和“纯洁”有关。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出一种极端保守主义的倾向。无怪乎埃斯普马克认为,当时的文学院“排斥处于领先地位的瑞典作家,并把最杰出的文学研究专家拒之门外”。这种选择背后,存在着一种在在黑格尔美学影响下形成的费舍尔的美学和布斯特罗姆的哲学。或者,更为具体的说,“理想的”(ideal)与“唯心主义的”(idealistic)被人们有意地或无意地混淆了。这两个词在中文中差别很大,而在英文中和瑞典文中,则只是词尾的变化而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趣味,瑞典文学院并不代表一种固定的美学思想,也不代表一种单一的审美标准。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对“理想倾向”的解读变得较为宽广。作家被要求具有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在他们为作家们写的评语中,那种由于不信神、对社会批判和冷嘲热讽而否定一位作家的词句不再出现了。这时,一种伟大的风格,史诗般描写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长篇巨制受到院士们的欢迎。可惜,这时托尔斯泰已经死了。我们今天常常听人用托尔斯泰未能得奖来批评瑞典文学院,其实,这恰恰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院士们自己的意见。他们对前一个时期评奖情况进行了检讨,取托尔斯泰这个典型的例子,以求实现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尽管如此,在这一阶段,对“理想”的解读使他们又一次未能及时站到文学发展的前列。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是现代主义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对此,瑞典文学院大体上持冷漠的态度。他们追求“伟大”的风格,反对“晦涩”的风格;重内容而不是重技巧。只是到了二战后,文学院的椅子由新一代院士们占据时,文学上的“开拓者”们才成了大奖的得主。我们看到,去领奖的变成了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聂鲁达这样一些人。这时,“理想”一词的解释变得更加自由,一个心照不宣的标准是文学性或艺术性,文学性上的创新精神。当索尔仁尼琴获奖时,人们对他的指责是,他的作品没有技巧上的创新,而这种指责,在前一个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诺贝尔并没有这么要求。尽管如此,诺贝尔所提出的那种“有益于人类”的“理想”仍然是获奖标准的底线。阿伦曾举例说,“如果作品赞同大屠杀,那么,不管它如何出色,也不符合遗嘱。”
自从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颁发以来,一个世纪过去了,坐在文学院那十八张椅子上的人离去一位就换上一位,授奖标准也随着院士们的新陈代谢而发生着或快或慢的变化。每年年初,一个由院士和从院外特邀成员共三至五人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要在四月份从约200名的“长名单”中挑出约15有中的“半长名单”。到了五月底,再从这个“半长名单”中挑出5名,成为“短名单”。这是院士们夏天的阅读任务。一个夏天读5个人的作品,仍是一件太累人的工作。好在这5个人中,常常有一半的人不是第一次进入短名单,他们的作品院士们过去读过。瑞典的夏天也不那么热,在海边游泳之余正好读书。九月中旬,院士们开始讨论,然而后就是十月份的投票。于是,种种机缘形成一股合力,最终一个人成了幸运者。有人赶上机会,得到了;有人生不逢时,又死得太早,文学院的标准还没有朝向有利于他的方向转化,于是就这么错过了。好在这个奖也不是一位作家文学地位的最终裁定,也没有人能够做这种裁定。文学有自己的命运。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仅仅是生活他们自己时代的一些比较有知识的凡人而已。他们不能超越时代的影响,有时甚至趣味比自己的时代还要保守。将他们神话化,再对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都是不切实际的。三瑞典文学院在评奖上似乎犯了不少错误,许多不该得奖的人得了,该得奖的人又没有得。如果我们现在搞一个二十世纪世界百名最优秀作家评选,再与实际得奖者对比一下,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异。这里面有瑞典文学院院士们看走了眼的原因,当然该检讨。在文学院内部,不同意见争论,后代院士对前代院士批评,都是常有的事。然而,他们评奖原则中有一条,却值得称赞。院士们要评活着的作家,没法像今人搞世纪回顾,当事后诸葛亮。不过,为了防止评错了人的现象,他们本来也可以采取一个较为保险的办法,那就是,等一位作家在一个国家取得绝对地位,或者已经取得世界声誉之后,再把奖授予他。如果这样的话,评错了人的情况会少得多,瑞典文学院也会少许多笑柄。何况,这也是一个省力得多的办法。既然这些作家已出了名,把他们的作品找来,翻一翻,了解一下基本内容,发现用评奖标准去套,还不致太离谱,就可以考虑定下来了。但他们不愿省
这个力气,而是确立了一个原则:从推动文学的发展和促进优秀文学家为全世界接受的角度来做这件事。他们认为,如果一位作家已经功成名就,获得了世界文坛的承认,这时,再授予他诺贝尔奖,仅仅是锦上添花而已,意义已经不大了。正像二十世纪初的一位院士颜尔纳所说,“文学院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主动从众多的作家中选出一位加以突出,这样做远比拿着钱袋子跟在一位已经公正地获得了‘世界声誉’的汉子后边增加他的遗产更为有价值。”院士们最想做的是,一位作家虽创作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但还没有引起文学界的普遍注意,或者,一位作家的虽获得了区域性的声誉,但没有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承认,这时,瑞典文学院慧眼识珠,发现了这位作家,将他推向世界。如果某一次,经过他们的发现、授奖,一位作家从此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承认,而这位作家的作品又恰恰配得到这种承认,这次授奖活动就做得很完美,实现了想实现的效果。确实,许多作家都是这样被他们推向世界的,特别是一些东方作家、拉美作家,过去在西方影响不大,经过他们的推荐,走向了世界。他们还想做的是,一位作家已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但还年富力强,有更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这个奖能帮助作家扫清以后创作道路上的从经济压力到社会承认方面的障碍,从而将作家造就成一代宗师。颜尔纳在推荐那位《骑鹅旅行记》的作者赛尔玛·拉格洛夫时,就曾写道,“她需要获得一种完全保障的地位,以便不再写那些浅显的故事和圣诞节小报上的文章。”这是说,有了这笔钱和这个名气,那些“大手笔”就可以专心去写“大气”的东西了。基于这样一些考虑,瑞典文学院倾向于一个做法:如果一位年轻的作家与年长的作家创作出在他们看来同样优秀的作品,那么,他们就更可能选年轻的那位。这样做,也许对年长的作家是一种不公平。年长的作家曾经错过得奖的机会,而他们却说,既然错过了就过去了,现在不再弥补。与其用一次获奖机会弥补过去的缺失,不如用它来对年富力强的作家进行扶植。这与我们常常见到的做法正好相反。我们总习惯于对年轻的人说,你以后的机会还多,先让年长的。用授奖来帮助作家获得这种声誉,而不对已获得的声誉进行承认,这么做的风险要大得多。这是一种伯乐所必须冒的风险。固然,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我们可以说,伯乐的确挑出了一些千里马,但
不能说,伯乐挑出的都必然是千里马。一位作家是否能获得“世界声誉”,受多种多样的因素影响,其中有作家的主观因素,也有种种客观的,作家不能左右的因素。大奖授给了一位作家,结果他并没有像院士们所期望的那样,被全世界普遍接受,被认为配得这个奖,这次授奖就开始被人们指责,这个奖的声誉也连带受影响,而继续冒这个险,就受到了压力。在一个世纪的漫长颁奖史上,这种压力不断出现,说瑞典文学院完全不受这种压力的影响,是不现实的。但是,让这个奖授得有用,坚持对正在发展着的世界文学的创作和接受过程的参予性,是他们的信念。为了这个信念,他们认为冒这个险值得。如果这是他们有时“选错人”的原因,他们则会说,只好如此了。四1938年的大奖授给了畅销书作家赛珍珠。赛珍珠获奖是由于她的《大地》对“中国农民生活作了丰富而准确的描写”。这部作品描写得是否丰富,是否准确,艺术水平如何,都是问题。赛珍珠的获奖,也许说明了瑞典文学院对中国的注意,然而,这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当时就有,而今天仍普遍存在的情况:许多描写中国而在西方引起轰动的作品,都谈不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而所有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近年来的一些优秀中国文学作品,在被翻译成西方文字后,影响却很小,仅在西方社会中的一个小小的东方文化爱好者圈子里为人所欣赏而已。这里面也许有商业性炒作的原因,但在这背后,更可能隐藏着东西方的趣味的深刻差异。东方人与西方人在文学评价标准上的确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位旅美作家,一位是林语堂,一位是张爱玲。对于中国人来说,张爱玲是一位比林语堂更加出色的作家。但对于许多圈外的西方人来说,林语堂几乎是那个年代的唯一的中国作家,而张爱玲,圈外人则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其实,张爱玲的英文也很好,在美国的几十年间也努力用英文写小说。林语堂的成功和张爱玲的不成功,当然与种种个人因素有关。但在这种种因素之外,仍有着一个是否善于迎合西方人口味的问题。对于中国作家,如果他生活在中国,用中文写作的话,是否善于迎合西方人口味,当然不能成为一条重要的标准。他们心目中的读者,应是生活在他周围的中国人,这些人是他的第一批读者。他创作的直接社会反响和经济回报,都是由这些读者提供的。但是,如果这位作家到了西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必须学
会取悦于生活在他周围的人,从他们那里获得社会反响和经济回报。作家的第一批读者使他能够生活下去,而第二批读者给他的是额外的名气。没有第一批读者,就不会引来第二批读者。文化的差异,因而带来的评价标准的不同,是不可避免的。但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认为,这种有差异的文化间并非完全不能沟通,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自我封闭,而是相互对话。我们需要对文化间的交叉点的承认,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仅仅是交叉点而已。将交叉点理解为最好,当作文学的最高追求,是一种价值的迷失和异化。在中国和世界华人文学界一次次等待,一次次失望之后,有人提议,我们可以设立一个自己的文学大奖,专奖世界华人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人家不给发奖,我们自己发。这种做法仍然小气。即使做出来,做成了,做出名气来,仍是一个语种的奖,还是比诺贝尔奖低一等。其实,世界文学奖并不规定只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要遵从捐赠人的意愿,但并非文学家的诺贝尔并不能为文学作最终立法,瑞典文学院院士们的趣味也并不能构成文学界唯一的世界法庭的最高标准。中国人要想搞,明智的做法是,也搞一个世界奖,由中国人评。这个奖的授予同样“不强调民族的归属”,同样“谁最有资格谁获得”,不局限于他是否是中国作家或用中文写作的作家。这个奖的评奖者如果能睁开眼睛,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世界,又不故意放进人为的偏见,把各国的真正优秀的作家评进来,从而也能在世界上建立影响,引起争论,让人们去赞扬、批评、咒骂、或作无所谓态的话,那么,这个奖就成功了。高建平2000年5月于望京
您可能关注的文档
- 维奈和达贝尔内模式下的别丢掉译文对比分析
- 呼伦贝尔市民主评议经济发展环境工作实施方案-总结报告-工作报告
- 日本科学家诺贝尔奖与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改革开放高校英语教育40年反思
- 针灸治疗贝尔面瘫研究进展
-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公示:江西诺贝尔化工硫有机化合物卤代烷烃酸紫外线吸收剂系列香料环评报告
- 2015大唐呼伦贝尔化肥有限公司招聘报名登记表及岗位表sere
- ———1999年诺贝尔化学奖简介
- 2017秋部编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第2课《首届诺贝尔奖版发》word教案
- 呼伦贝尔草原、蒙兀室韦、林城根河、兴安林区生态4日游
- 高二生物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1
- 高二生物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2
- 纽约时报杨振宁催生2013年物理学诺贝尔奖上帝粒子
- 呼伦贝尔疾病预防控制2007年第四期
-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 福禄贝尔的幼儿教育思想及其启示(froebel'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ought and its enlightenment)
- 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百年回眸
- 2009年呼伦贝尔市查漏补种
- 规律与启示_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20世纪重大科学成就看科技原始创新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