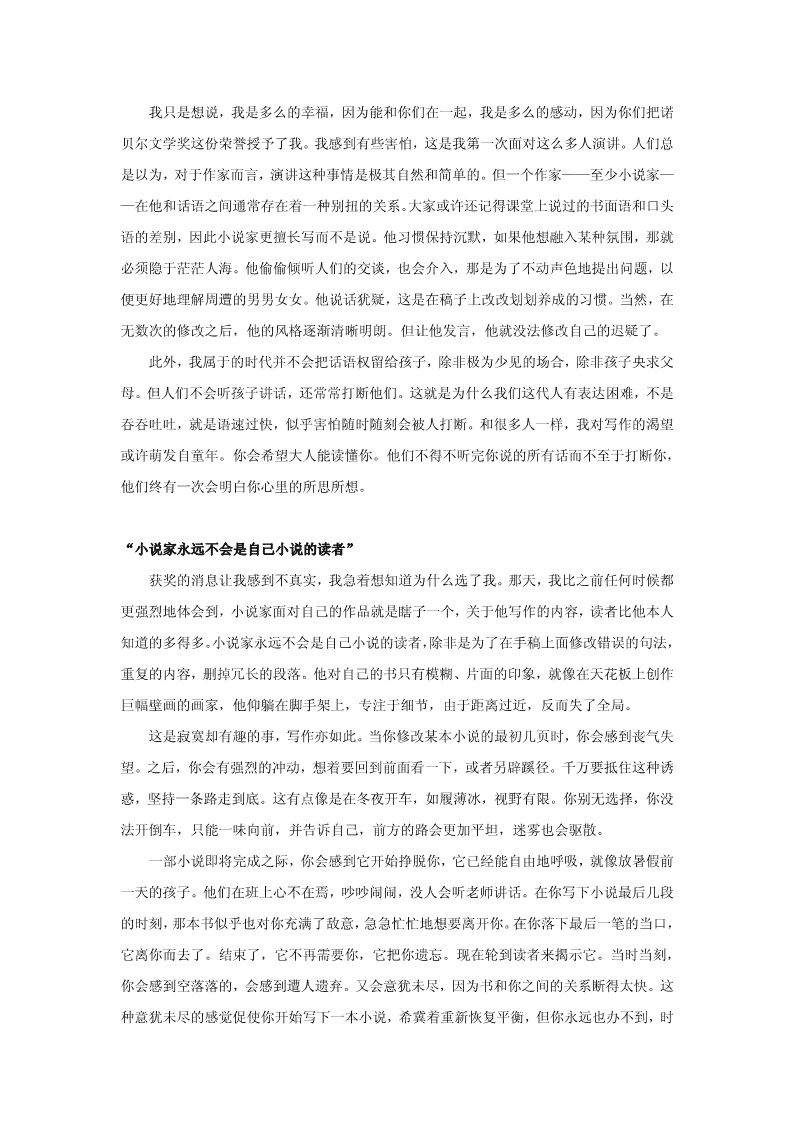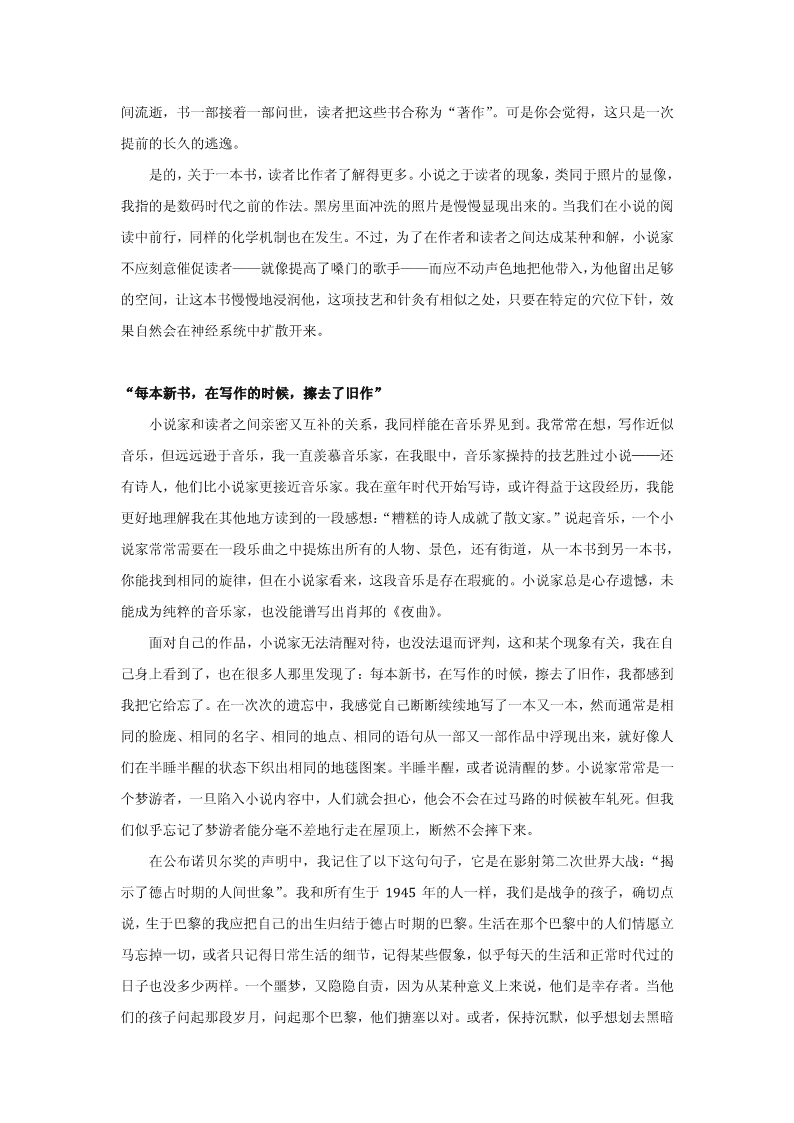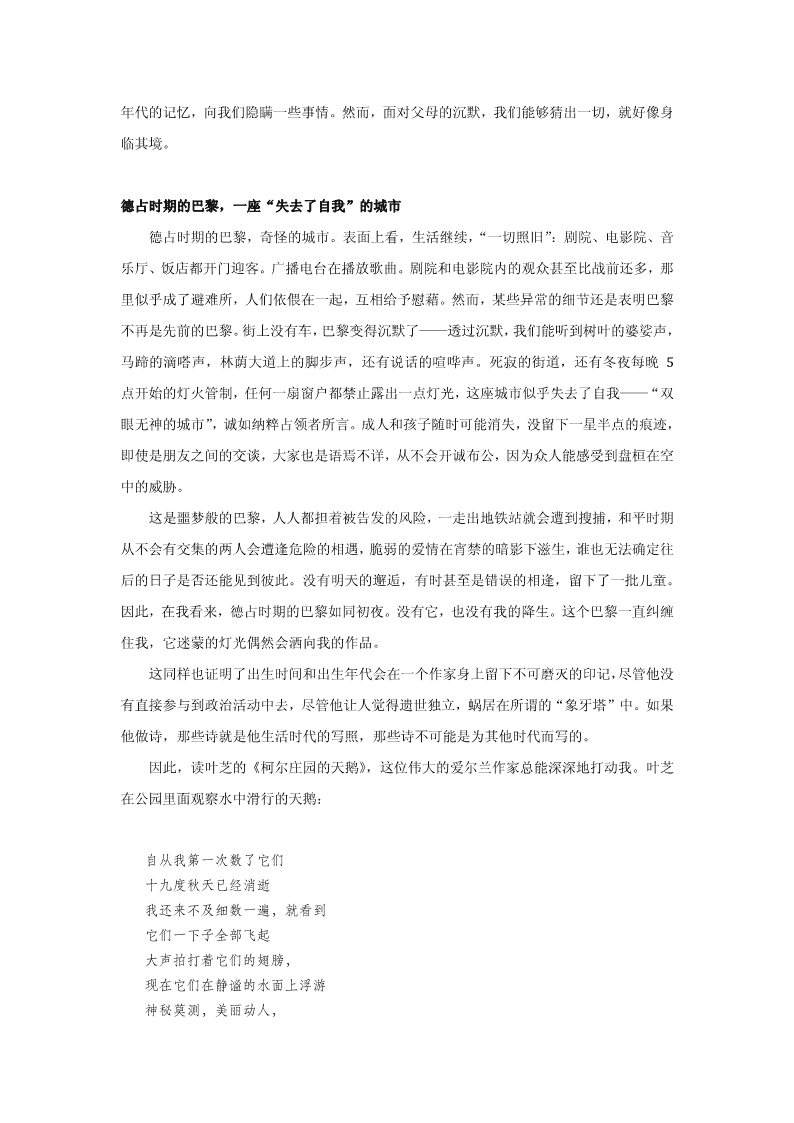- 318.80 KB
- 2022-06-16 12:30:12 发布
- 1、本文档共5页,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可选择认领,认领后既往收益都归您。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先通过免费阅读内容等途径辨别内容交易风险。如存在严重挂羊头卖狗肉之情形,可联系本站下载客服投诉处理。
- 文档侵权举报电话:19940600175。
我只是想说,我是多么的幸福,因为能和你们在一起,我是多么的感动,因为你们把诺贝尔文学奖这份荣誉授予了我。我感到有些害怕,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演讲。人们总是以为,对于作家而言,演讲这种事情是极其自然和简单的。但一个作家——至少小说家——在他和话语之间通常存在着一种别扭的关系。大家或许还记得课堂上说过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别,因此小说家更擅长写而不是说。他习惯保持沉默,如果他想融入某种氛围,那就必须隐于茫茫人海。他偷偷倾听人们的交谈,也会介入,那是为了不动声色地提出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周遭的男男女女。他说话犹疑,这是在稿子上改改划划养成的习惯。当然,在无数次的修改之后,他的风格逐渐清晰明朗。但让他发言,他就没法修改自己的迟疑了。此外,我属于的时代并不会把话语权留给孩子,除非极为少见的场合,除非孩子央求父母。但人们不会听孩子讲话,还常常打断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代人有表达困难,不是吞吞吐吐,就是语速过快,似乎害怕随时随刻会被人打断。和很多人一样,我对写作的渴望或许萌发自童年。你会希望大人能读懂你。他们不得不听完你说的所有话而不至于打断你,他们终有一次会明白你心里的所思所想。“小说家永远不会是自己小说的读者”获奖的消息让我感到不真实,我急着想知道为什么选了我。那天,我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体会到,小说家面对自己的作品就是瞎子一个,关于他写作的内容,读者比他本人知道的多得多。小说家永远不会是自己小说的读者,除非是为了在手稿上面修改错误的句法,重复的内容,删掉冗长的段落。他对自己的书只有模糊、片面的印象,就像在天花板上创作巨幅壁画的画家,他仰躺在脚手架上,专注于细节,由于距离过近,反而失了全局。这是寂寞却有趣的事,写作亦如此。当你修改某本小说的最初几页时,你会感到丧气失望。之后,你会有强烈的冲动,想着要回到前面看一下,或者另辟蹊径。千万要抵住这种诱惑,坚持一条路走到底。这有点像是在冬夜开车,如履薄冰,视野有限。你别无选择,你没法开倒车,只能一味向前,并告诉自己,前方的路会更加平坦,迷雾也会驱散。一部小说即将完成之际,你会感到它开始挣脱你,它已经能自由地呼吸,就像放暑假前一天的孩子。他们在班上心不在焉,吵吵闹闹,没人会听老师讲话。在你写下小说最后几段的时刻,那本书似乎也对你充满了敌意,急急忙忙地想要离开你。在你落下最后一笔的当口,它离你而去了。结束了,它不再需要你,它把你遗忘。现在轮到读者来揭示它。当时当刻,你会感到空落落的,会感到遭人遗弃。又会意犹未尽,因为书和你之间的关系断得太快。这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促使你开始写下一本小说,希冀着重新恢复平衡,但你永远也办不到,时
间流逝,书一部接着一部问世,读者把这些书合称为“著作”。可是你会觉得,这只是一次提前的长久的逃逸。是的,关于一本书,读者比作者了解得更多。小说之于读者的现象,类同于照片的显像,我指的是数码时代之前的作法。黑房里面冲洗的照片是慢慢显现出来的。当我们在小说的阅读中前行,同样的化学机制也在发生。不过,为了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达成某种和解,小说家不应刻意催促读者——就像提高了嗓门的歌手——而应不动声色地把他带入,为他留出足够的空间,让这本书慢慢地浸润他,这项技艺和针灸有相似之处,只要在特定的穴位下针,效果自然会在神经系统中扩散开来。“每本新书,在写作的时候,擦去了旧作”小说家和读者之间亲密又互补的关系,我同样能在音乐界见到。我常常在想,写作近似音乐,但远远逊于音乐,我一直羡慕音乐家,在我眼中,音乐家操持的技艺胜过小说——还有诗人,他们比小说家更接近音乐家。我在童年时代开始写诗,或许得益于这段经历,我能更好地理解我在其他地方读到的一段感想:“糟糕的诗人成就了散文家。”说起音乐,一个小说家常常需要在一段乐曲之中提炼出所有的人物、景色,还有街道,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你能找到相同的旋律,但在小说家看来,这段音乐是存在瑕疵的。小说家总是心存遗憾,未能成为纯粹的音乐家,也没能谱写出肖邦的《夜曲》。面对自己的作品,小说家无法清醒对待,也没法退而评判,这和某个现象有关,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也在很多人那里发现了:每本新书,在写作的时候,擦去了旧作,我都感到我把它给忘了。在一次次的遗忘中,我感觉自己断断续续地写了一本又一本,然而通常是相同的脸庞、相同的名字、相同的地点、相同的语句从一部又一部作品中浮现出来,就好像人们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织出相同的地毯图案。半睡半醒,或者说清醒的梦。小说家常常是一个梦游者,一旦陷入小说内容中,人们就会担心,他会不会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轧死。但我们似乎忘记了梦游者能分毫不差地行走在屋顶上,断然不会摔下来。在公布诺贝尔奖的声明中,我记住了以下这句句子,它是在影射第二次世界大战:“揭示了德占时期的人间世象”。我和所有生于1945年的人一样,我们是战争的孩子,确切点说,生于巴黎的我应把自己的出生归结于德占时期的巴黎。生活在那个巴黎中的人们情愿立马忘掉一切,或者只记得日常生活的细节,记得某些假象,似乎每天的生活和正常时代过的日子也没多少两样。一个噩梦,又隐隐自责,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幸存者。当他们的孩子问起那段岁月,问起那个巴黎,他们搪塞以对。或者,保持沉默,似乎想划去黑暗
年代的记忆,向我们隐瞒一些事情。然而,面对父母的沉默,我们能够猜出一切,就好像身临其境。德占时期的巴黎,一座“失去了自我”的城市德占时期的巴黎,奇怪的城市。表面上看,生活继续,“一切照旧”:剧院、电影院、音乐厅、饭店都开门迎客。广播电台在播放歌曲。剧院和电影院内的观众甚至比战前还多,那里似乎成了避难所,人们依偎在一起,互相给予慰藉。然而,某些异常的细节还是表明巴黎不再是先前的巴黎。街上没有车,巴黎变得沉默了——透过沉默,我们能听到树叶的婆娑声,马蹄的滴嗒声,林荫大道上的脚步声,还有说话的喧哗声。死寂的街道,还有冬夜每晚5点开始的灯火管制,任何一扇窗户都禁止露出一点灯光,这座城市似乎失去了自我——“双眼无神的城市”,诚如纳粹占领者所言。成人和孩子随时可能消失,没留下一星半点的痕迹,即使是朋友之间的交谈,大家也是语焉不详,从不会开诚布公,因为众人能感受到盘桓在空中的威胁。这是噩梦般的巴黎,人人都担着被告发的风险,一走出地铁站就会遭到搜捕,和平时期从不会有交集的两人会遭逢危险的相遇,脆弱的爱情在宵禁的暗影下滋生,谁也无法确定往后的日子是否还能见到彼此。没有明天的邂逅,有时甚至是错误的相逢,留下了一批儿童。因此,在我看来,德占时期的巴黎如同初夜。没有它,也没有我的降生。这个巴黎一直纠缠住我,它迷蒙的灯光偶然会洒向我的作品。这同样也证明了出生时间和出生年代会在一个作家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尽管他没有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尽管他让人觉得遗世独立,蜗居在所谓的“象牙塔”中。如果他做诗,那些诗就是他生活时代的写照,那些诗不可能是为其他时代而写的。因此,读叶芝的《柯尔庄园的天鹅》,这位伟大的爱尔兰作家总能深深地打动我。叶芝在公园里面观察水中滑行的天鹅:自从我第一次数了它们十九度秋天已经消逝我还来不及细数一遍,就看到它们一下子全部飞起大声拍打着它们的翅膀,现在它们在静谧的水面上浮游神秘莫测,美丽动人,
可有一天我醒来,它们已飞去。哦它们会筑居于哪片芦苇丛、哪一个池边、哪一块湖滨,使人们悦目赏心?(裘小龙)译天鹅的形象经常出现在19世纪的诗歌中,比如波德莱尔,比如马拉美。但叶芝的诗不可能成于19世纪。它独特的节奏,它的伤感忧郁,独属于20世纪,甚至就是他写诗的那年。21世纪的作家偶尔会感到自己是时代的囚徒,阅读19世纪伟大作家的作品——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他泛起怀旧之情。在那个时代,时间比现在流逝得更为缓慢,这种缓慢恰巧和小说家的工作相得益彰,因为他能更好地集中精力和注意力。此后,时间加快了脚步,疾驰而奔,这也解释了文学作品的差异,过去是恢宏庞大的故事,如同构建大教堂,现在是断断续续、零敲碎打的小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属于转承启合的一代,我也好奇,我们的后辈,那些伴着网络、手机、电子邮件、推特而生的人会如何运用文学来表达他们的世界,其中的每个人永远处于“在线状态”,“社会关系”侵犯了私隐和秘密,而直到最近,秘密仍是我们的个人财产——秘密赋予了个体以深度,它还是小说的重要题材。不过,关于文学的未来,我愿意持乐观态度,我相信明日的作家会接过交接棒,从荷马开始,每代作家都是如此……此外,作家和其他艺术家一样,不用刻意地和自己的时代连为一体,因为这联系本就紧密得无从逃脱,他唯一能呼吸的空气,是人们所说的“时代气息”,他在作品中会展现出一些超越时间的东西。在上演拉辛或莎士比亚的剧本时,演员是穿古装,还是听凭导演的要求穿上牛仔裤和皮夹克,这都无关紧要。都是无伤大雅的细节。阅读托尔斯泰的时候,我们不会记得安娜·卡列尼娜穿的是1870年的裙子,尽管相隔一个半世纪,她离我们还是如此的近。还有一些作家,如爱伦·坡、梅尔维尔或司汤达,在去世两百年后,现代人倒比他们的同代人能更好地理解他们。“托尔斯泰可以将天空和景色融为一体”归根结底,小说家应保持多少距离?游离于生活之外描写生活,因为假如你沉溺其中——沉溺在情节中——你只能得到模糊的影像。然而,在面对自己创造的人物,以及那些从真实生活中脱胎而来的男男女女的时候,这轻盈的距离并不会妨碍小说家体认的能力。福楼拜
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当托尔斯泰在俄罗斯的一个火车站,看见那个女人跳入夜间火车下,他立即能感同深受。这种体认的天赋还能走得更远,托尔斯泰可以将天空和景色融为一体,他能吸纳一切,及至安娜·卡列尼娜轻轻闪动的睫毛。这种第二状态1和自恋是相反的两码事,因为它既要忘我又要全神贯注,唯有如此才能感知到最小的细节。这同样意味着一种孤独。这种孤独并不是蜷缩自我,而是达到一定程度的专注和清朗,从而将外部世界移植到自己的小说中去。我一直认为,面对湮没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体,面对看似平淡无奇的事物,诗人和小说家能赋予它们神秘感——只要努力观察它们,用近乎催眠的方式。在他们的目光之下,日常生活最终会蒙上一层迷云,并闪烁出幽幽磷光,这是初看之下不会察觉的,它隐藏在深处。诗人和小说家的责任即在于此,画家也是,揭开每个人深处的秘密和磷光。我想起了远房表亲——画家莫迪利亚尼,他的画作最让人动容之处就是他会挑选一些无名氏做模特,街头顽童和女孩、女仆、农村小孩、年轻的学徒。他用尖锐的笔触刻画这些人物,令人联想起托斯卡纳的伟大传统、波提切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他还赋予了他们——或者说,彰显出——隐藏在卑微外表之下的优雅和高贵。小说家的工作也是同样的意义。他的想象力并非歪曲现实,而是潜入现实的深处,将其显现,如同红外线和紫外线一般发现隐藏在表象之下的东西。我差不多认为,最佳情况下,小说家就是通灵者,甚至是预言家。如同地震仪,随时记录最细微的脉动。在阅读我喜爱的作家的传记之前,我总是犹犹豫豫。传记有时过于专注细节,那些并不精确的记述,令人困惑或失望的性格刻画,这一切让我想到了收音机里传出的杂音,它会干扰电台节目的播送,模糊了音乐或声音。只有阅读他们的小说能让我们走进作家的隐秘,这才是最好的他,他会低声向我们诉说,而他的声音也不会受到任何噪音的干扰。不过,读了作家的传记,我们有时会发现童年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会是他今后小说的雏形,而他本人却不会清醒地意识到这点,标志性的事件会一次次回来,幻化成不同的样子,萦绕在他的书中。现在,我想到了希区柯克,他不是作家,但他的电影具备小说的张力和内核。在希区柯克5岁时,父亲让他送封信给他的朋友,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孩子把信交给了局长,而后者把他关进牢房,那里晚上是用来关押各种轻罪犯人的。孩子怕得要死,他等了一小时,局长才把他放出来,并对他说:“如果你行为不端,你知道等着你的是什么了。”警察局长教育孩子的方式着实古怪,或许就是这个诱因促成了我们之后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1是指一种精神状态,某些作家在写作时会进入这种状态,同时将抽象和凝练结合在一起。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常运用此法写作。
感受到的悬疑不安的氛围。“要到很多年后,我才感到我的童年是个谜”但愿我的个人经历不会让你们感到厌烦,我觉得我童年的几个阶段可以看作是我之后小说的雏形。我常和父母分隔两地,他们把我托付给朋友照料,而我对这些朋友一无所知,住所和寄居的房子一直在变动。在那时候,一个孩子是不会对任何事感到惊讶的,尽管身处在怪异的环境中,他也觉得一切正常。要到很多年后,我才感到我的童年是个谜,我试图知道更多,从父母托付的形形色色的人身上,从不停更换的地点中。然而,我无法得知大多数人的真实身份,我也无从精确地定位过往的那些地点和居所。我要解谜却从未成功,我要洞穿秘密,这份决心赋予了我写作的欲望,似乎写作和想象能最终帮助我解开这些谜团,这些秘密。既然说到“秘密”,自然会想到19世纪的一部法国小说——《巴黎的秘密》。正巧是巴黎,我的故乡,这个大城市和我童年最初的印象联系在一起,这些印象太过深刻,此后的我只是在不停地挖掘“巴黎的秘密”。大概从八九岁起,我就独自漫步于街头,我害怕迷路,但我越走越远,前往未知的街区,前往塞纳河的右岸。这是在白天,这能让我安心。步入青春期之后,我努力克服恐惧,乘上地铁开始夜间冒险,前往更遥远的街区。就这样,人们认识了自己的城市。我是在效仿我崇拜的多数作家,从19世纪开始,所谓的大城市——是指巴黎、伦敦、圣彼得堡、斯德哥尔摩——就是他们写作的背景和主题之一。短篇小说《人群中的人》中,爱伦·坡首次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浪,他在咖啡馆玻璃后面观察人浪前仆后继地涌上人行道。他注意到一个外表奇特的老人,于是在夜间尾随老人前往伦敦不同的街区,想要知道更多关于他的事。但无名氏就是“人群中的人”,跟踪也是徒劳之举,因为他永远无名无姓,人们永远无法获得更多关于他的信息。他不是作为个体存在,他只是人潮汹涌的过客中的一个,他们紧紧挨在一起或者互相推搡,在街头迷失了自我。“在城市地图的帮助下,你的一生都能印刻在记忆中”我还想起了诗人托马斯·德·昆西的青年时代,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在伦敦牛津街的人潮中,他结识了一名年轻女孩,这只是大城市中的一次偶然邂逅。女孩陪他消磨了数天时光,他终会离开伦敦。一个星期之后,两人约定:她会在每晚的同一时间在蒂奇菲尔德街的街角等待他。但两人再也没有碰面。“肯定有无数次,我们在同一时间穿过伦敦这个巨大的迷宫寻觅对方;或许我们相隔仅18米——却远得注定永久分离。”
对于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而言,年岁流转,城市的每个街区、每条马路都能勾起一段回忆、一次相遇、一份悲伤、一段欢乐时光。同一条路通常能勾连起数段记忆,因此在城市地图的帮助下,你的一生能都印刻在记忆中,层层叠叠,就像是在隐迹纸本上辨认重叠的字迹。别人的生活同样如此,还有千千万万陌生人的生活,他们在高峰时刻的马路和地铁走廊上相遇。因此,青年时代的我为了帮助自己写作,会翻出老旧的巴黎黄页,特别是那种人名按路名索骥的,还会标上楼房号码。纸页翻过,我觉得在双眼注视下,对巴黎进行了一次X射线检查,但这是一座隐没的城市,如同亚特兰蒂斯,我能嗅到时间的气息。时光流逝,那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唯一留下的印迹,就是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地址、他们的电话号码。年复一年,某个人名有时就消失不见了。翻动从前的电话薄,会让我有恍惚感,想到有些电话号码再也没人接听了。在此之后,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一首诗中的段落又击中了我:我回到了我的城市。它曾是我的眼泪,我的脉搏,我童年种疼的腮腺炎。彼得堡……你还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可以查寻死者的声音(王家新)译是的,在翻阅巴黎老黄页的时候,我有了最初写作的冲动。我要做的就是用铅笔画出陌生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想象他们的生活,在数百万、数百万的名字当中。我们会在大城市中迷路或失踪。我们还能改换身份,过上新生活。我们可以投身一次漫长的调查,找寻某人的蛛丝马迹,而起因可能只是失落街区的一两个地址。调查文件上的只言片语总是在我的心中引起共鸣:最后已知的居所。失踪、身份、时间流逝,这些主题和大城市的地图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自19世纪起,大城市成了小说家耕耘的领地,其中最杰出的几位也常常和某个城市成为了一体:巴尔扎克和巴黎,狄更斯和伦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圣彼得堡,东京和永井荷风,斯德哥尔摩和雅尔玛·索德伯格。我的那代人受到上述作家的影响,他们愿意一探波德莱尔所说的“古都的曲径僻巷”。当然,50年过去了,我是说从在我青年时代算起,在那时候,和我同龄的青年人在认识自
己城市的过程中会萌生强烈的感触,现在的城市已然变样。有些是在美洲,有些是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城市变成了令人惶惶不安的“特大城市”。居民孤立无援地生活在遗忘的街区中,社会战争的氛围笼罩周围。贫民区越来越多,越来越触手可及。及至20世纪,小说家眼中的城市还是带有一丝“浪漫”的,和狄更斯还有波德莱尔笔下的城市并无多大差别。我很想知道未来的小说家将在虚构的著作里面如何描写这些人口稠密的城市巨无霸。生于1945年“让我对记忆和遗忘的题材更加敏感”宽容的你们宣称我的作品“运用回忆的艺术,唤起最难以捉摸的人类命运”。这是谬赞了。这份独有的记忆和我的出生日期有关——1945年,是它驱使我去收集那些陌生人留存于世的过往的残片、细微的线索。生于1945年,城市被摧毁,大量人口失踪,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这个年份让我对记忆和遗忘的题材更加敏感。只可惜,我们无法再像普鲁斯特那样,借助耐力和坦诚来追寻逝去的时光。普鲁斯特笔下的社会还是稳定的,是19世纪的社会。普鲁斯特的回忆是在细枝末节中浮现往昔岁月,就像一幅生动的绘画。而我感到现在的记忆更加不确定,它要不停地和遗忘抗争。在遗忘的覆盖之下,我们只能捕捉到往事的残片、中断的线索、逐渐消失且几乎难以捉摸的人类命运。但或许这就是小说家的天职,面对遗忘的巨大白页,让模糊得只剩一半的只言片语重新浮现出来,就像在海洋上漂流的冰山。(原文版本来自《世界报》,段落划分也是参照《世界报》)黄小涂译2014年12月11日
您可能关注的文档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谈当
-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石林业一中高一英语 Module One Unit3同步练习(无答案) 牛津译林版必修1
-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石林业一中高一英语 Module Two Unit2同步练习(无答案) 牛津译林版必修2
- 一:诺贝尔医学奖
- 诺贝尔城活动方案
- 奥苏贝尔认知同化理论作业
- 为诺贝尔写颁奖词
- 关于贝尔的翻译过程模式_蒋显文
- 双重断裂的代价_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_之三_
- 2018_2019学年五年级语文上册第六单元21诺贝尔作业设计(无答案)苏教版
- 2018_2019学年五年级语文上册第六单元21诺贝尔教案设计苏教版
- 呼伦贝尔市初中毕业考试
- 呼伦贝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覆盖工程技术实施方案
- 诺贝尔陶瓷专卖店导购员培训07版
- 诺贝尔__课件
- 诺贝尔用课件
- 呼伦贝尔投资项目立项申请报告
- 伊莎贝尔上市期媒体投放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