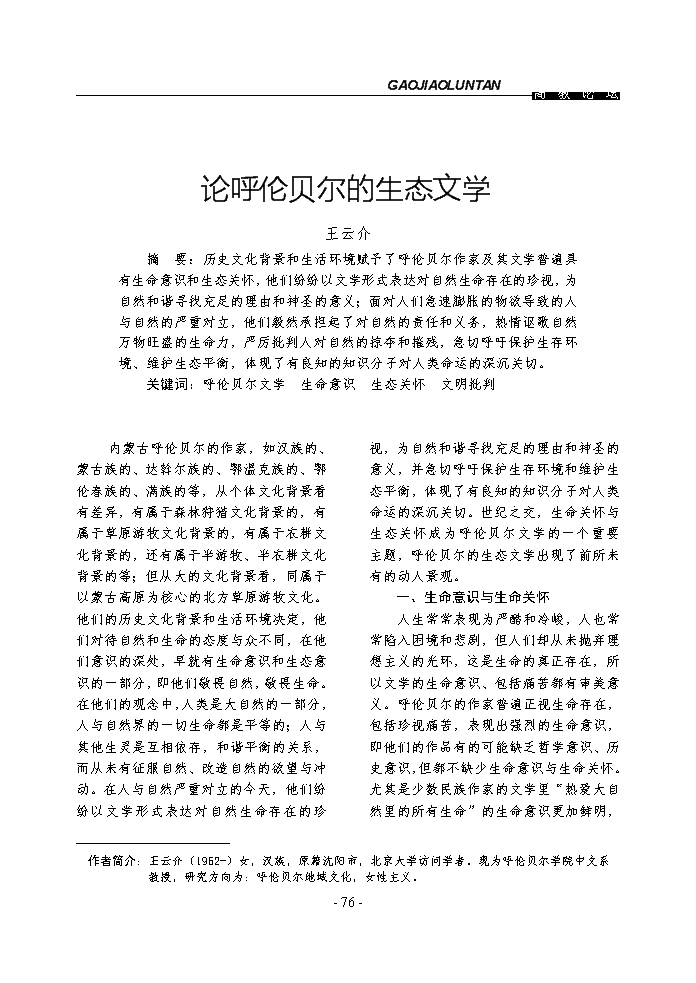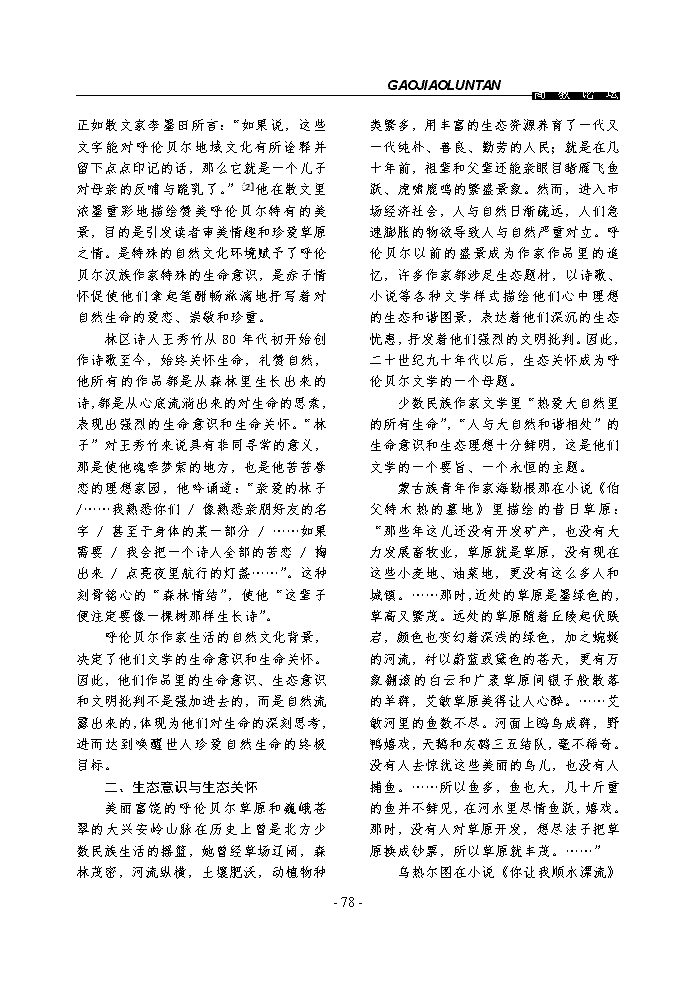- 48.00 KB
- 2022-06-16 12:01:28 发布
- 1、本文档共5页,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可选择认领,认领后既往收益都归您。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先通过免费阅读内容等途径辨别内容交易风险。如存在严重挂羊头卖狗肉之情形,可联系本站下载客服投诉处理。
- 文档侵权举报电话:19940600175。
GAOJIAOLUNTAN高教论坛论呼伦贝尔的生态文学王云介摘要:历史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赋予了呼伦贝尔作家及其文学普遍具有生命意识和生态关怀,他们纷纷以文学形式表达对自然生命存在的珍视,为自然和谐寻找充足的理由和神圣的意义;面对人们急速膨胀的物欲导致的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他们毅然承担起了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热情讴歌自然万物旺盛的生命力,严厉批判人对自然的掠夺和摧残,急切呼吁保护生存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体现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人类命运的深沉关切。关键词:呼伦贝尔文学生命意识生态关怀文明批判-81-GAOJIAOLUNTAN高教论坛作者简介:王云介(1962-)女,汉族,原籍沈阳市,北京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呼伦贝尔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呼伦贝尔地域文化,女性主义。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作家,如汉族的、蒙古族的、达斡尔族的、鄂温克族的、鄂伦春族的、满族的等,从个体文化背景看有差异,有属于森林狩猎文化背景的,有属于草原游牧文化背景的,有属于农耕文化背景的,还有属于半游牧、半农耕文化背景的等;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同属于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他们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决定,他们对待自然和生命的态度与众不同,在他们意识的深处,早就有生命意识和生态意识的一部分,即他们敬畏自然,敬畏生命。在他们的观念中,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人与其他生灵是互相依存,和谐平衡的关系,而从未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欲望与冲动。在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的今天,他们纷纷以文学形式表达对自然生命存在的珍视,为自然和谐寻找充足的理由和神圣的意义,并急切呼吁保护生存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体现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人类命运的深沉关切。世纪之交,生命关怀与生态关怀成为呼伦贝尔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呼伦贝尔的生态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人景观。一、生命意识与生命关怀人生常常表现为严酷和冷峻,人也常常陷入困境和悲剧,但人们却从未抛弃理想主义的光环,这是生命的真正存在,所以文学的生命意识、包括痛苦都有审美意义。呼伦贝尔的作家普遍正视生命存在,包括珍视痛苦,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即他们的作品有的可能缺乏哲学意识、历史意识,但都不缺少生命意识与生命关怀。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里“热爱大自然里的所有生命”-81-
GAOJIAOLUNTAN高教论坛的生命意识更加鲜明,这是他们文学的一个要旨、一个永恒的主题。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小说里的人物、动物以及一切生物都以生命的神圣性存在着,尤其是鄂温克老人,他们熟悉林子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条河,每一块石头,每一条小径,甚至每一棵草,每一滴露珠。例如《老人和鹿》里的老人,他带着孩子走进森林,边走边抚摩它们、和它们说话,他告诉孩子:“这里的河、树、鸟儿、鹿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帮助过我,帮我活到现在。”他每年都要来这里住上几天,听野鹿的鸣叫,看太阳从野鹿身后升起来的美景,他说林子里的声音才是真正的歌。河、树、鸟儿、鹿等动植物在森林鄂温克人的眼里都是可爱的、生动的生命,是与他们相依相伴、亲密无间的朋友;人只是众多生物中的一员,而不是其他生物的主宰。在达斡尔族女作家昳岚的文学里,自然世界里所有的生命都是可贵的,她形象地告诉人们:人应该珍惜、爱怜这些可爱的生命,而不应该轻易放弃、伤害他们。她的散文《情萦苍穹》对母亲生命消逝充满了痛惜与自责的情感,对母亲的深爱、悔恨与自责浸透在字里行间。《像梦里的钟声》抒写了一位母亲因为痛失爱子而无限的惆怅与哀伤,她每天都失魂落魄地去荒野里呼唤幼子的亡灵。“母亲”这种生命角色震颤读者的灵魂,令人感叹母亲的神圣和伟大,遗憾生命的脆弱与无常。《寻叶晚秋》写一只不幸的小花牛,摔断了一条后腿,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它“溜园的眼睛总是哀哀的,揪得我的心疼。”它哀哀的眼神与小主人心痛的表情做了一次人与动物互为相通的交流,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回归到了一个世界。呼伦贝尔的少数民族作家对生态保护的认识是与生俱来的,即对自然和谐的认识不是受20世纪末世界生态文学浪潮的冲击形成的,更不是从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得来的,而是从草原或森林里带出来的。他们是游牧或狩猎这个独特的文化群体中的一员,属于这个群体顽强留存下来的文化。他们是拥有丰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呼伦贝尔真正的主人。例如,在鄂温克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有一种敬畏自然的独特品性,他们的神灵崇拜,生活细节,处处都“渗透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对山野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为了生存,森林中的鄂温克人以多种方式寻求自身的救赎,或者说在精神上他们以低姿态,同丛林其它生物置于精神对等的地位。例如,在鄂温克人崇拜的诸神中,有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蛇、野鸡、小鸟、松鼠、驯鹿,还有用松树的枝条制作的多种象征物;除去对幼小生灵象征物的崇拜,自然还有对食肉类生物猞猁、狼和食草类生物鹿、獐、狍的崇拜。……”[1]所谓“敬畏”和“精神对等”只能和“和谐”“平衡”“相互依存”相联系,而决不会与“对立”“冲突”“掠夺”“征服”有牵连。呼伦贝尔是一个多种经济共生、多种文化并存之地,除了本土原生的少数民族蒙古族、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汉族居民在历史的进程里也陆续融入了这片绿野,化作了呼伦贝尔草原的子民,正如人们所说“一部草原文化史就是一部多民族互相交融、共同进步的历史”-81-
GAOJIAOLUNTAN高教论坛。汉族作家同少数民族作家一样是以赤子的情怀和勤劳的双手描绘着这里的一切的,为呼伦贝尔文学的繁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散文家李墨田所言:“如果说,这些文字能对呼伦贝尔地域文化有所诠释并留下点点印记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反哺与跪乳了。”[2]他在散文里浓墨重彩地描绘赞美呼伦贝尔特有的美景,目的是引发读者审美情趣和珍爱草原之情。是特殊的自然文化环境赋予了呼伦贝尔汉族作家特殊的生命意识,是赤子情怀促使他们拿起笔酣畅淋漓地抒写着对自然生命的爱恋、崇敬和珍重。林区诗人王秀竹从80年代初开始创作诗歌至今,始终关怀生命,礼赞自然,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从森林里生长出来的诗,都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对生命的思索,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关怀。“林子”对王秀竹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那是使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也是他苦苦眷恋的理想家园,他吟诵道:“亲爱的林子/……我熟悉你们/像熟悉亲朋好友的名字/甚至于身体的某一部分/……如果需要/我会把一个诗人全部的苦恋/掏出来/点亮夜里航行的灯盏……”。这种刻骨铭心的“森林情结”,使他“这辈子便注定要像一棵树那样生长诗”。呼伦贝尔作家生活的自然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文学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关怀。因此,他们作品里的生命意识、生态意识和文明批判不是强加进去的,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体现为他们对生命的深刻思考,进而达到唤醒世人珍爱自然生命的终极目标。二、生态意识与生态关怀美丽富饶的呼伦贝尔草原和巍峨苍翠的大兴安岭山脉在历史上曾是北方少数民族生活的摇篮,她曾经草场辽阔,森林茂密,河流纵横,土壤肥沃,动植物种类繁多,用丰富的生态资源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纯朴、善良、勤劳的人民;就是在几十年前,祖辈和父辈还能亲眼目睹雁飞鱼跃、虎啸鹿鸣的繁盛景象。然而,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人与自然日渐疏远,人们急速膨胀的物欲导致人与自然严重对立。呼伦贝尔以前的盛景成为作家作品里的追忆,许多作家都涉足生态题材,以诗歌、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描绘他们心中理想的生态和谐图景,表达着他们深沉的生态忧患,抒发着他们强烈的文明批判。因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生态关怀成为呼伦贝尔文学的一个母题。少数民族作家文学里“热爱大自然里的所有生命”,“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意识和生态理想十分鲜明,这是他们文学的一个要旨、一个永恒的主题。蒙古族青年作家海勒根那在小说《伯父特木热的墓地》里描绘的昔日草原:“那些年这儿还没有开发矿产,也没有大力发展畜牧业,草原就是草原,没有现在这些小麦地、油菜地,更没有这么多人和城镇。……那时,近处的草原是墨绿色的,草高又繁茂。远处的草原随着丘陵起伏跌宕,颜色也变幻着深浅的绿色,加之蜿蜒的河流,衬以蔚蓝或黛色的苍天,更有万象翻滚的白云和广袤草原间银子般散落的羊群,艾敏草原美得让人心醉。……艾敏河里的鱼数不尽。河面上鸥鸟成群,野鸭嬉戏,天鹅和灰鹤三五结队,毫不稀奇。没有人去惊扰这些美丽的鸟儿,也没有人捕鱼。……所以鱼多,鱼也大,几十斤重的鱼并不鲜见,在河水里尽情鱼跃,嬉戏。那时,没有人对草原开发,想尽法子把草原换成钞票,所以草原就丰茂。……”-81-
GAOJIAOLUNTAN高教论坛乌热尔图在小说《你让我顺水漂流》里,描画了一幅“人与动物共舞”的生态理想图:一个夏天,萨满卡道布老爹在林子里做桦皮船,他预知尼胡利要来,就给尼胡利找好了伴儿——一只野兔、一只小鹿和一头大母熊。平日与人不能“和平共处”的野兽,因为有了卡道布老爹的存在而与他们在一起玩了整整一天。这是多么兴旺的生命图景、多么美好的生态家园啊!达斡尔族女作家苏华在散文《凯河人》里回忆了鄂嫩家族在凯河建立村庄的原因:“当鄂嫩家族的车队经过一条江叉子时,江叉子中的鲫鱼竟纷纷夹在大轱辘车的辐条中被带出江面,又随着车轮滚动弹跃着,返回江水中,一时间银光闪闪,数不清的鲫鱼跃出水面——鄂嫩家族部落便选这条江叉子的南岸驻足下来,建立起了村庄。”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态图景啊,作家希望我们的后代能够生活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充分感受生命的自由与美好。李墨田曾登上“运5”飞机,俯瞰呼伦贝尔草原,思考“圆印文化”,那令人兴奋又刻骨铭心的经验,让读者羡慕不已:“蒙古包是花蕊,哈栅是花瓣。梅花初时为白色,一个多月过去渐黄,几个月后变暗,隔年就能还原草色,有的还长出蘑菇圈,浓浓的绿格外醒目。时值初秋时节,草枯眼疾,我们看到几乎到处都盛开着深浅不一的梅花,而尤以濒水之地为最多,数也数不清。这是‘逐水草而居’的结果。”这些美的经验和描述,形神兼备,情理统一,成为诗意范本。作家们以情溢于言,理胜于辞的潮水般的愤激与忧患,唤醒人们对现实的思考和善待家园的态度。王秀竹的诗《一种精神的绿化过程》《面对森林》《染绿的散句》《关于绿化问题》《中国大兴安岭之冬》等,都是从他心底喷发出来的对绿色文明的畅想与礼赞,对绿色灾难的痛楚与忧患,抒发的是一个敏感而正义的诗人希冀世界美好和人与自然和谐的激情。面对森林的人为灾难,他自然生发出一种不能抚慰的心灵痛楚和不可遏止的社会批判力量。他诗歌的情愫有对森林无限的缠绵爱恋,有对绿色无边的畅想珍藏,有“自然铁律”在“现代进程中”已经出现“危机和恐慌”的告诫与警策,有面对“一截截/独对残阳”的伐根的疼痛与揪心,有“曾经剥夺了”林子“一茬茬爱情和创作权”的自省与自责,有“种植一棵树/就是在种植我们自己”的责任和期待,有“我要在发芽的文字里/开始一种情绪的返青”的告白和信念,有用“比森林更木质的声音/完成一首诗歌的呐喊”和呼吁,有“循着绿色的原则/在和谐的路上完成发芽的行走”的展望和憧憬……他的诗没有丝毫的技术痕迹,而是诗人心灵的流淌、宣泄和呐喊,是对生态危机的深刻思考。诗的抒情主体既是一个敏感多思的诗人,又是肩负着社会历史使命的理想主义者。他对生态灾难做了最含蓄也最透彻的诠释,对人类无情摧毁森林的暴力行为,作出了最沉郁也最激烈的谴责与批判。三、社会关怀与文明批判-81-
GAOJIAOLUNTAN高教论坛在呼伦贝尔作家的意识深层里还普遍存在社会关怀与文明批判。这和他们的历史传统、文化形态也不无关系,无论游牧文化,狩猎文化,森林文化,甚至农耕文化,这些文化群体里的作家,早已形成了亲和大自然、崇拜大自然的心理,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他们深刻懂得人与自然亲合,彼此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对立,彼此都受损伤。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并毅然承担起了对自然、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以文学形式,热情讴歌自然万物旺盛的生命力,严厉批判人对自然的掠夺和摧残,急切地呼吁保护生存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体现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人类命运的深沉关切。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学还在被浓重的悲剧气氛笼罩的时候,乌热尔图就在1978年的小说《森林里的歌声》里,以“桦树上的婴儿”、“布谷鸟一样的鄂温克姑娘”乌娜吉形象,清脆地唱出了兴安岭密林的歌声,流露出了人类与大自然完美融合的生态渴望。在后来的小说里,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理论批评文章中,他这种生态意识越来越明晰、生态思想越来越成熟、生态关怀越来越强烈,以至形成了他自己的生态理念。他深刻地认识到:“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物多样化受到严重破坏,大量的濒危野生动物面临灭绝,人类的生存环境趋于恶化,大自然濒临失衡状态,人类已毫无退路地站在历史性抉择的交叉点,境况如同莎士比亚的那句对白:生存还是毁灭?”[3]除了以话语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外,他还在许多场合强烈呼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坚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呼伦贝尔自然生态环境,力求保护和恢复森林、草原、湿地、河流的自然生态。在20世纪末的中国作家中,乌热尔图是一个较早以文学形式思考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作家,他的作品也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苏华在散文集《母鹿·苏娃·代前言》里说:“1998年6月和8月两次嫩江特大洪水的无情袭击,与其说是大自然的警告和惩罚,莫如说那是几千几万几亿株树木和草株的眼泪,更是那些丧失了生息之地的野生动物们的咆哮和怒吼!”她担忧被迫滞留在杜拉尔境内的那只孤独而忧伤的鹿,能不能回到它的群体里去,她说:“我希望我们的后代能够生活在青山绿水的怀抱中,生活在湛蓝的天空下……”。苏华对大自然和人类充满爱心,对大自然与人类正面临的严重的生态灾难满怀焦虑。满族作家袁玮冰近年对生态问题十分关注,着力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作品里流露着鲜明的生态关怀和文明批判。被《小说选刊》转载的小说《红毛》,获得了索龙嘎奖的小说《大鸟》等都是优秀的生态小说。他的小说情景交融、意境深邃,融进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他说:“《红毛》写得我荡气回肠。”他采用了人格化手法,写一个黄鼬家族的毁灭,在黄鼬身上加进了人类的爱憎情仇,其强烈的主观情感和丰富的艺术想像,使小说产生了一种精神震撼力。他指出,人类为满足一己私欲对野生动物进行蚕食,这是对野生动物的暴行,这些鲜活的可爱的生命在人类的威逼下生存是十分艰难的。-81-
GAOJIAOLUNTAN高教论坛海勒根那,新近写的小说如《父亲鱼游而去》《寻找青鸟》等精神指向与叙事策略与以往(《到哪儿去,黑马》)截然不同,他明显放弃了激越强硬的文本实验,开始采用幻想的方式对现实与历史进行虚构与创造。他采用了边缘化叙述人的叙述策略,努力重聚历史和文明的碎片,强烈向往理想的生态模式,使我们依稀觉察到他对人类当下生存的物质与精神问题的迫切关注。发表在《青年文学》2004年第1期上的《父亲鱼游而去》是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作品,作家在小说结尾处明确指出:“仅以此文祭奠我故乡于2002年干涸的莫力庙水库”。小说描写的父亲吃贝壳、沙土、有脚蹼能游水等特异功能,乍一看令人不可思议,已经不具备传统“父亲”的内质,其实这些细节与人类对水的渴望和焦虑密切相关,作家在这里暗示了人类与水的难解之缘和人离开水的生存困境。作家在无限的人生苦难中加进了生存忧患情绪,小说的意境是外部险恶的环境引起的主体心灵的反应,大河干涸、洪水泛滥无疑都是人与自然对立与冲突的结果。李墨田在《大地之印·跋》中也抒写了生态忧患,他说:“大自然的色彩由浓变淡,原生态文化渐次消失,而它们是我们人类赖以生息的摇篮,是中华大文化链条中值得仰视的一环,不能不让每一位有良知的文化人为之忧虑。”面对现实生活中“私捕滥捞”、“砍伐猎杀”之风,作家沉重地感叹到“我们有过许多竭泽而渔的悲剧,人是这悲剧的作者,也是读者。”(《昔日金飘带》)在具体描绘时,作者触景生情、悲从中来:“一株株百年落叶松就是在这旋律中倒下,溅起飞扬的雪浪。留下来的是圆圆的树桩。圆圆的树桩上露出圆圆的年轮,圆圆的年轮间冒出圆圆的树液,那分明是大树的眼泪。”作者进一步用细腻的情感和触目惊心的艺术形象告诫人们:“一棵棵树桩静静地戳立在山地上,极像书画的印章。它们或高或矮、或明或暗、或坚或腐,显然有的已阅历了一个树的轮回期。这些山之印腐而不倒,似乎在印证着什么,诉说着什么,警示着什么,这只有今人或许能够领悟。”(《大地之印》)用中国传统的“绿色思想”来解释,人与自然亲合,彼此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对立,彼此都受损伤,而人受损的不只是生态环境,而且还有心灵和本性。大环境生存的危难和个体求索的痛苦,加强了作家心理的紧张度,因而,在呼伦贝尔作家的意识深处,最关心的是环境的严重异化和人对自然的态度问题。他们把自己当作自然的儿子,像儿子热爱、善待母亲一样,热爱、善待自然母亲。呼伦贝尔这块广袤富庶的土地养育了各个民族的作家,各个民族的作家也都在努力为这片故土、为人类创造着优秀的精神财富,也都在努力通过自己文学的优质对其他文化产生良好的影响。参考文献:[1]乌热尔图,你让我顺水漂流·丛林幽幽,作家出版社,1996:239。[2]李墨田,《大地之印·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491。[3]乌热尔图,骏马文学,依偎在大自然怀抱的新人,2000:5.70。-81-GAOJIAOLUNTAN高教论坛-81-
您可能关注的文档
- 呼伦贝尔市健康教育基本职责
- 景观设计公司比对(贝尔高林 vs edsa)
- 论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分布特徵与2004年获奖成果的科学贡献
- 纽贝尔监舍音视频门禁管理实施方案
- 纽贝尔银行门禁及库包管理实施方案
- 呼伦贝尔草原产草量动态变化研究——以新巴尔虎右旗为例
- 两种疗法对恢复期贝尔氏麻痹血瘀证的临床疗效对比研究
- 呼伦贝尔学院教学评价
- 分期针刺治疗贝尔面瘫的临床研究
- 呼伦贝尔移动网络构建策略与规划方案研究
- 呼伦贝尔大草原歌曲_歌曲歌词_歌手介绍
- 呼伦贝尔学院会计学专业学分制下学风建设的思考
- 呼伦贝尔草原特色旅游现状及开发策略研究
-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原子结构和原子光谱
- 大班绘本故事《贝尔熊很害怕》
- 呼伦贝尔学院建筑工程学院结构力学试卷
- 呼伦贝尔市总工会2012“春风行动”活动总结
- 2011年内蒙古呼伦贝尔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