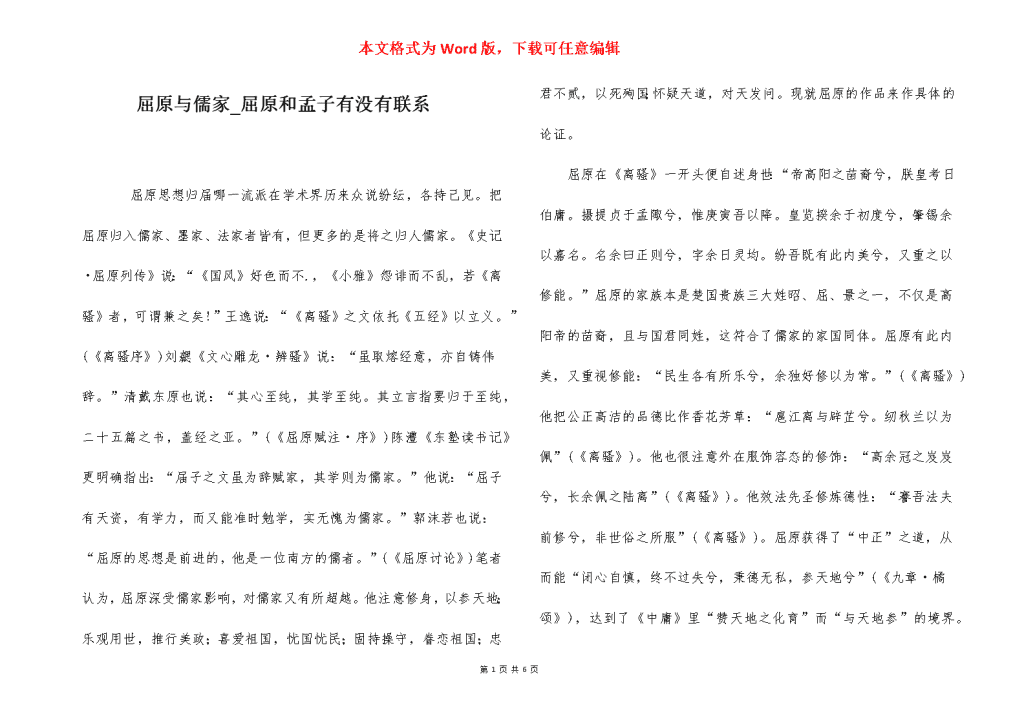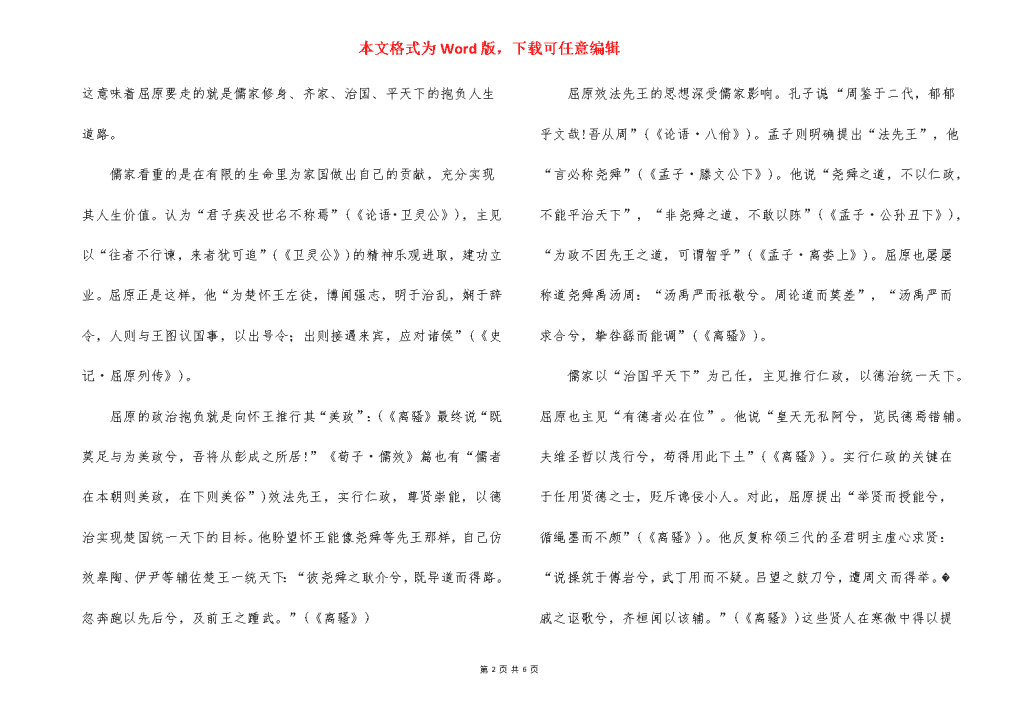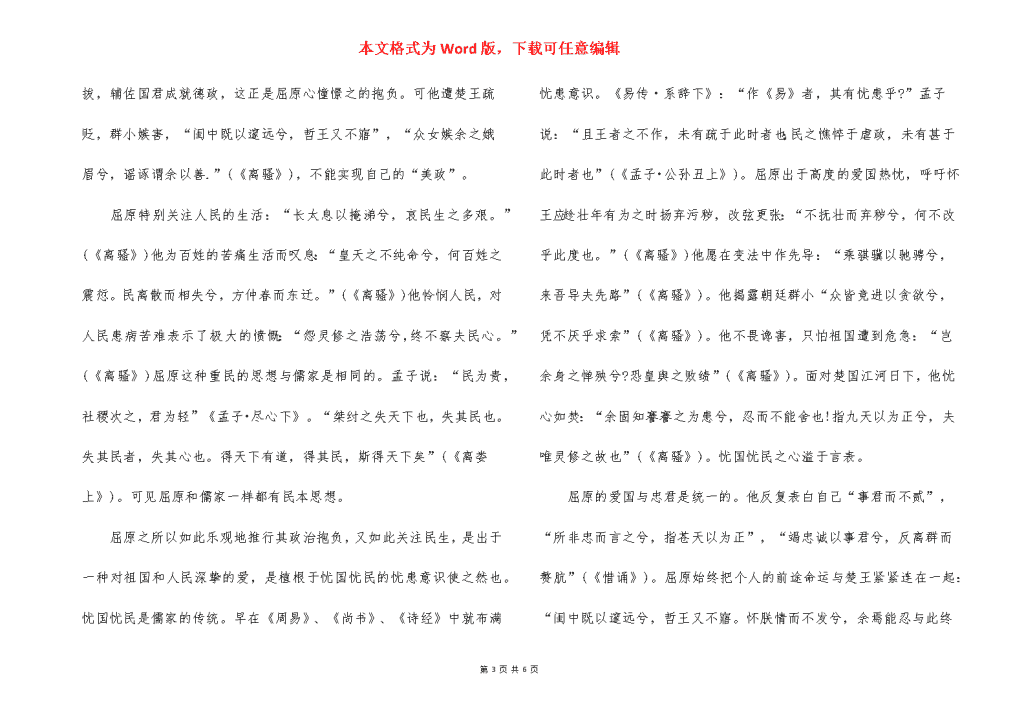- 23.26 KB
- 2022-06-16 12:13:06 发布
- 1、本文档共5页,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可选择认领,认领后既往收益都归您。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先通过免费阅读内容等途径辨别内容交易风险。如存在严重挂羊头卖狗肉之情形,可联系本站下载客服投诉处理。
- 文档侵权举报电话:19940600175。
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屈原与儒家_屈原和孟子有没有联系 屈原思想归届哪一流派在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把屈原归入儒家、墨家、法家者皆有,但更多的是将之归人儒家。《史记・屈原列传》说:“《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王逸说:“《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离骚序》)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清戴东原也说:“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屈原赋注・序》)陈澧《东塾读书记》更明确指出:“届子之文虽为辞赋家,其学则为儒家。”他说:“屈子有天资,有学力,而又能准时勉学,实无愧为儒家。”郭沫若也说:“屈原的思想是前进的,他是一位南方的儒者。”(《屈原讨论》)笔者认为,屈原深受儒家影响,对儒家又有所超越。他注意修身,以参天地;乐观用世,推行美政;喜爱祖国,忧国忧民;固持操守,眷恋祖国;忠君不贰,以死殉国;怀疑天道,对天发问。现就屈原的作品来作具体的论证。第6页共6页
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 屈原在《离骚》一开头便自述身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日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的家族本是楚国贵族三大姓昭、屈、景之一,不仅是高阳帝的苗裔,且与国君同姓,这符合了儒家的家国同体。屈原有此内美,又重视修能:“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他把公正高洁的品德比作香花芳草:“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他也很注意外在服饰容态的修饰:“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离骚》)。他效法先圣修炼德性:“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离骚》)。屈原获得了“中正”之道,从而能“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九章・橘颂》),达到了《中庸》里“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的境界。这意味着屈原要走的就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人生道路。 儒家看重的是在有限的生命里为家国做出自己的贡献,充分实现其人生价值。认为“君子疾没世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主见以“往者不行谏,来者犹可追”(《卫灵公》)的精神乐观进取,建功立业。屈原正是这样,他“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来宾,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的政治抱负就是向怀王推行其“美政”:(《离骚》最终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成之所居!”《荀子・儒效》篇也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则美俗”)效法先王,实行仁政,尊贤崇能,以德治实现楚国统一天下的目标。他盼望怀王能像尧舜等先王那样,自己仿效皋陶、伊尹等辅佐楚王一统天下:“彼尧舜之耿介兮,既导道而得路。忽奔跑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离骚》) 屈原效法先王的思想深受儒家影响。孔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则明确提出“法先王”,他“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下》)。他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孟子・公孙丑下》),“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孟子・离娄上》)。屈原也屡屡称道尧舜禹汤周:“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离骚》)。第6页共6页
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 儒家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主见推行仁政,以德治统一天下。屈原也主见“有德者必在位”。他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离骚》)。实行仁政的关键在于任用贤德之士,贬斥谗佞小人。对此,屈原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他反复称颂三代的圣君明主虚心求贤:“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这些贤人在寒微中得以提拔,辅佐国君成就德政,这正是屈原心憧憬之的抱负。可他遭楚王疏贬,群小嫉害,“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离骚》),不能实现自己的“美政”。 屈原特别关注人民的生活:“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他为百姓的苦痛生活而叹息:“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离骚》)他怜悯人民,对人民患病苦难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屈原这种重民的思想与儒家是相同的。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离娄上》)。可见屈原和儒家一样都有民本思想。 屈原之所以如此乐观地推行其政治抱负,又如此关注民生,是出于一种对祖国和人民深挚的爱,是植根于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使之然也。忧国忧民是儒家的传统。早在《周易》、《尚书》、《诗经》中就布满忧患意识。《易传・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说:“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屈原出于高度的爱国热忱,呼吁怀王应趁壮年有为之时扬弃污秽,改弦更张:“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离骚》)他愿在变法中作先导:“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他揭露朝廷群小“众皆竞进以贪欲兮,凭不厌乎求索”(《离骚》)。他不畏谗害,只怕祖国遭到危急:“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面对楚国江河日下,他忧心如焚:“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离骚》)。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第6页共6页
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 屈原的爱国与忠君是统一的。他反复表白自己“事君而不贰”,“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肮”(《惜诵》)。屈原始终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楚王紧紧连在一起:“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离骚》)屈原在这点上和儒家并不完全相同。孔子是主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论语・八佾》)。屈原是孔子的信徒。而孟子则主见“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公孙丑下》)。另外,儒家的忠君并不是忠于一个君主,他们主见“从道不从君”。屈原所处的时代,仁人贤士遇上“壅主”许多都是“良禽择木而栖,俊杰择主而仕”的。儒者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学说主见,孔孟之徒周游列国,荀子朝秦暮楚。可屈原却超越了这一点。他出身于楚国王室,与君主同姓,国事即是家事,家国一体,他必定要与楚国共存亡。他对君主竭尽忠贞,对楚王的疏远也表示过生气,也曾产生过“去国”的想法:“欲高飞而远集”(《惜诵》)。但他并没有走,他执著于自己的抱负,誓与祖国共存亡。当抱负破灭后,他仿效彭咸投江自沉,以死殉国。正如司马迁所说:“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睹顾楚国,系心怀王,.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列传》)第6页共6页
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 在对待昏君“壅主”的态度上,屈原和儒家的人生哲学是完全不同的。儒者“志于道”(《论语・述而》),修好己身,待时而动,依据环境的变化打算自己的进退出处。孔子主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儒家注意在坚持原则的状况下,因地制宜,特殊注意“权”:“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以道事君,不行则止”(《先进》)。孟子主见:“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上》)在遇到无道昏君时,儒者往往独善其身。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论语・述而》)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朱熹说“孔颜乐处在于安贫乐道”即是指此。儒家的独善其身并非如道家那样避世,而是避乱世昏君,蓄势待发,等待治世明君。可是屈原却不能接受儒家这一人生才智,他执著于自己的抱负,决不改易操守:“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他没有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而是以死去抗争:“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虽不周于今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第6页共6页
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 屈原的天道观也深受儒家的影响。儒家重人事,轻天命,重理性,关注现实政治和伦理道德。孔子罕言性与天命,“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不求知天”,“敬鬼神而远之”(《雍也》),“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将鬼神生死置于不论之列。孔子也常呼“天”:“噫!天丧予!天丧予”,“知我者其天乎”(《宪问》)。这说明孔子敬“天”,更重视人事,是一位理性主义者。孟子表面上也承认天的存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但他更重视主观精神:“尽其心而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荀子则认为应当“明天人之分”,“天行有常”,与人世.没有什么必定的联系,并进一步提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主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但荀子也说过“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等信“天”的话。屈原“本质上对于神的存在是怀疑的”(郭沫若《屈原讨论》)。《天问》一整篇一百七十多问,涉及自然界的天体演化,人类.的风风雨雨,民族的存亡兴衰,诗人以“问难”的方式提出。正如鲁迅先生《摩罗诗力说》中所说:屈原“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他问“天极焉加?”“九天之际,安放安属?”表示了对自然的“天”的怀疑。他又从历史的深切反思中,表示了对“天命”的怀疑:“授殷天下,其位安始?”“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皇天集命,惟何戒之?”但“他在另一方面却仍保留着天的信奉”(郭沫若《屈原讨论》)。他从自己诞生时日的巧合(“寅年寅月寅日”)感觉自己禀受了“天”所给予的内美。他还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离骚》),“雄雄赫赫,天德明只”(《大招》)。“他反对‘怪力乱神’,但也讴歌‘怪力乱神”’(郭沫若《屈原讨论》),像《九歌》里他讴歌鬼神。这一点应当从艺术上来论证,从南北方文化的融合上来说,屈原的作品是楚地巫文化融会人北方中原文化的产物。他标榜的尧舜禹汤,主见的“仁政”。对“天”的怀疑,都是中原儒文化的精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说:“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娥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弹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洒不废,沈湎日夜,举以为欢,荒.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这说明屈原作品的精神实质是儒家的经典,是楚民族的风俗、习性、语言和北方儒文化的精神构成了其宏大的诗篇。 编校 郑艳第6页共6页